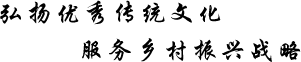许绍棣(1900-1980),字萼如,临海县(今临海市)张家渡人。复旦大学商科毕业。1928年,任浙江省立高级商业学校(即发展至今的浙江工商大学)校长,继任国民党浙江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是浙江CC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兼设计委员,旋奉派赴欧考察,回国后于1934年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主持浙江省教育厅10余年。鉴于战时浙江各大学均内迁,1939年主持筹办浙江战时大学,旋改英士大学,兼任校务委员会主任,认为"教育之基础,奠自小学,而小学之良莠,端在教师,故师范专业训练,实最重要"。
在施政10多年中,以扩充师范教育为中心工作,订定第一、第二两期师范教育实施方案,划定全省师范教育区,添设省立师范学校,督促各县普设县立师范或简易师范学校,指派师范生到各县服务,并提高其待遇。奖励举办师范及职业学校。于是各县举办师范及简师之风因之大盛,全省共有54所之多。1946年离职,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东南日报》杭州分社社长。1949年去台湾,1980年病故。
抗战前,许绍棣和他日本留学时期的同学郁达夫夫妇之间有着较多交往,两家之间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应邀工作于福建省政府,夫人王映霞则避乱于丽水。当时鳏身带着2个孩子的许绍棣也恰巧随浙江教育厅移署丽水。乱世之中,任何正常的举动往往都会受到猜忌与扭曲,因此而流言四起。最终造成了郁、许之间的矛盾以及郁达夫夫妇之间的离异。但也有资料称,许绍棣与孙多慈的结识,却正是当时王映霞的介绍。
于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同样经历了人生与情感风雨的许绍棣与孙多慈在他们交往了两年之后,终于结婚了,并生养了两个男孩,了结了夙缘,得到了不管怎么说都还算是宁静的归宿。对于孙多慈来说,徐悲鸿毕竟是她的初恋,分手又是由于外在因素,因此夙愿难谐的怅惘自是难免。1946年春,经历抗战-归来而稍得片刻宁静的她自然又忆及悲鸿先生。此时徐悲鸿也已与廖静文在北平正式结婚。于是在一幅红梅图轴中,孙多慈题道:“倚翠竹,总是无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的词句,流露出她当时怅惘的情怀。悲鸿先生见后,只在梅枝上补了一只没有开口的喜鹊,似乎也表示着自己对彼此之间欲说还休的无奈和对各自人生归宿的默默祝福。
从孙多慈婚后的经历来看,她的生活和绘画专业应该还是受到许绍棣许多的关心与照顾。当时许绍棣是浙江省教育厅长兼国立英士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主任。婚后,深知孙多慈艺术造诣的他就把其聘为英士大学讲师,后又聘为国立杭州艺专副教授。1947年,孙多慈在上海举办展览,1949年随许绍棣迁居台湾,1951年在台北、香港举办个展。那时的许绍棣已任台湾-、成为台湾政坛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了。后来,孙多慈又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后去法国国立美术学院从事研究。回台湾后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并于1957年获台湾教育部美术类金像奖,后任该校艺术学院院长。如果没有许的关照,一个柔弱女子要在那样的纷繁乱世中得到这样的成就又谈何容易。也有资料说孙多慈是温厚和婉,事亲孝,待友诚,“与之相对,如沐春阳,如饮醇醪,无人不觉她可爱。”像这样的女子,虽说与许绍棣没有很深的爱情基础,但起码应该还是维系着一份并非一般的亲情。
1947年,许绍棣与孙多慈的第二个男孩出生。为了表达他的欣喜,许绍棣自拟了五言古诗一首,遍寄了他的亲朋友好。其中就有:“…万籁正无声,欻闻龙虎吼……儿其泰来时,此乐应不朽”等句。
1953年9月,徐悲鸿在北京病逝。巧合的是,孙多慈恰巧在中山堂看画展中碰到了蒋碧薇,并在与蒋碧薇唯一一次谈话中得知徐悲鸿的死讯。于是,孙多慈就在家中为徐悲鸿守孝三年。虽说徐悲鸿是孙的业师,但同时却也是孙的初恋情人。许绍棣能让孙在家中为其守孝并达3年之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是极尽仁厚与宽容了。
从许家临海亲戚了解到,在20世纪四十年代战火分飞的乱世中,孙多慈没有与许一起回过临海。1949年去台之后,孙多慈除了在台湾定居外,也大多在世界各地游历与讲学。1970年代初,孙多慈因患癌症3次赴美开刀治疗,最后于1975年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其生平好友,号称物理女王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家中。
虽然,孙多慈经历了那么多的情感波折,但是她却仍然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且卓有成就的女画家之一。早年在随徐悲鸿学画时,她的素描就很见功夫,也有称之为国内第一名手的。1935年,因悲鸿先生的提携,中华书局为她印行《孙多慈素描集》。宗白华先生作序称之“落笔有韵,取象不惑,好像生前与造化有约,一经晤面,即能会心于体态意趣之间,不惟观察精确,更能表现有味,是真能以艺术为生命为灵魂者。”又说她“观察敏锐,笔法坚实,清新之气,扑人眉宇。” 1937年,孙多慈参加南京第二届全国美展中,作品“石子工”从创作思想到手法上都延续了徐悲鸿写实风格的影响。
与许绍棣婚后,感情生活复归平静的孙多慈游历了国外诸如意大利庞贝古城、法国巴黎等艺术之都,参观了流落异国他乡、陈列于别人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尤其是中国敦煌壁画后,受其感动与艺术感染,画风渐变。从艺术品拍卖市场上能见到的孙多慈油画作品来看,其早期艺术手法确实与徐悲鸿如出一辙,用笔坚实而厚重,造型准确传神。而后期作品则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她的用笔变得跳跃了,松秀而灵动,色调斑斓多姿,技法上具备了印象派对于瞬息光影变化与内心感觉的捕捉,但画幅上却依然体现了女性画家特有的性灵中的澹远宁静之美。
在台湾,孙多慈还被认为是全能的天才卓荦的画家,因为她除了油画上的造诣之外,国画的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等也无不工妙,画鹅更号称台湾一绝。正如大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注重生活化的写生一样,孙多慈也将其准确的素描造型能力引入国画,开创国画写实一种新的生动的面貌。也正如宗白华所称赞的“引中画更近自然,恢复踏实的形体感”。但是,孙多慈写实中国画的风格却并没有摒弃中国画最根本的技法与精神。她的水墨线条依然是纯粹的“写”得的,精神中依然充溢着中国化的潇散诗意与高远气韵。
孙多慈去世后,晚年许绍棣默默地守着挂满四壁的孙多慈画作,孑然一身的他更觉得亲人逝去的悲哀。而去国离乡,“望故乡之渺渺”的现实也使其心境倍感凄凉。曾见其集-句的《乡情》:“几多人物在他乡,枕绕泉声客梦凉。白首思归归不得,海天东望夕茫茫。”及《八十感怀》诗句:“览镜白头嗟耄及,可怜归计日迟迟”,叹尽了孤身一人且归期无望的愁绪与感伤。
去世的前几天,病榻上的许绍棣还写了一首《踏莎行》(寄诸好友):“一室羁栖,孤零滋味,伤心触景情先醉,人生安乐总无方,凭栏不觉洒清泪。”然而,这一次却竟然是词未竟,人已逝。1980年,许绍棣病死台湾,死后与孙多慈的骨灰合葬在阳明山。这也最终了却了那些情海波澜的恩恩怨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