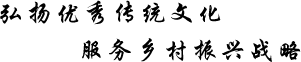傅雷(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艺术翻译家。本县渔潭乡(今下沙乡王楼村)人。
傅雷(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艺术翻译家。本县渔潭乡(今下沙乡王楼村)人。1919年,入周浦镇小学,第二年考入上海南洋附小四年级,1921年转至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会学校),读至初中一年级,因反迷信宗教,被学校开除,后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1927年冬,傅雷在表兄顾仑布的协助下赴法留学,他一面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一面在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同时攻读美术理论、艺术批评。留法期间,曾游历比利时、瑞士、意大利。
1931年秋返回祖国,被聘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主讲美术史和法文。1932年1月和朱梅馥结婚。1933年辞去美术专科学校教务。1934年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抗日战争期间,傅雷在上海一面从事外国文学译著工作,一面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文艺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反对美蒋发动内战的阴谋,傅雷奔走呼号,与马叙伦、陈叔通等发表宣言,筹备成立了“中华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第一届理事。新中国成立后,傅雷被推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书记等职,积极从事文学写作和翻译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革”中,傅雷遭到“-”的残酷破孩,于1966年9月3日,和夫人一起含冤离开人世。
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和杰出的翻译家。他一生翻译外国文学名著33部,著译约500万言。他的译作严格遵循“信、达、雅”原则,他说:“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他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座右铭,对译作精益求精。解放前,他译过《托尔斯泰传》,可是解放后不愿再版,他说:“我看过托尔斯泰几部作品呢?我不该这样轻率从事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是他抗日战争期间的译作,解放后,1952年重择一次,1963年又作一次大修改。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长达百万言,他从1936年开译,至1939年译毕,花了3年功夫。解放后,他竟又花费2年时间重译这部名著!他一生在书斋中度过,在辛勤的笔耕中度过,长期在他家工作的保姆周菊娣说:“傅先生每天早上8点起床,9点到12点半工作,下午2点又坐到书桌前,7点才吃晚饭。晚上看书、写信到深夜。”他以其翻译与研究巴尔扎克著作的卓越成就,被聘为法国巴尔扎克研究协会会员。以其辛勤劳动的硕果,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树立起一块金光闪闪的丰碑。
傅雷是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自从错划为“右派”以后,他深居简出,闭门著译,仍然为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日夜笔耕。其时,他的爱子傅聪在波兰留学,1959年学业期满,为了免受父亲的牵累,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傅雷乍听这个消息,“像一座木雕似的,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半晌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接连3天,不思饮食。本身是“右派”,儿子又“叛国”,使傅雷遭受双倍的横祸。在傅雷最困难的时候,中央领导人通过组织传话给他:“各人做事各人当,不会连累他,请他放心。”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还表示:“祖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傅聪开着,只要愿意回来,欢迎。”傅雷的灰冷的心中燃起炽热的希望之火,他一封一封信飞往伦敦,谆谆教导儿子勿忘祖国,永远维护祖国的尊严。
“孩子,十个月来(傅聪出走后,傅雷十个月没给儿子写信——作者注)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你的负担。你既然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有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
“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然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
他的爱国之心,跃然纸上。1961年,组织上给博雷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傅雷不会说谎,他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却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1966年,一场灾难降临中国大地,傅雷首当其冲。8月30日,上海音乐学院的“-”、“造反派”来抄傅雷的家,连花园都被挖地三尺,后来在一只锁着的小箱子里,查到一面老掉牙的小镜子,背面嵌着蒋介石像;一本旧画报,印有宋美龄的照片。“大右派窝藏反党罪证!”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跪倒在地,这箱子是姑母寄存在他家的,但傅雷不能实说,他怕连累别人,只是反复申述那不是他的箱子,这当然过不了关。9月2日,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戴着高帽子,站在长凳上示众,当天夜里,夫妇上吊自杀,他在遗书中说:“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
他含冤愤然离开人世。但是,他仍然相信党,深切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党和祖国也没忘记他,1979年4月26日,上海文联和上海作协为傅雷夫妇平反昭雪,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