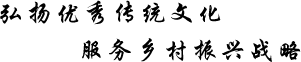崔子忠,字道母(梁清标《画谱序》亦作“道毋”),原籍山东省莱阳县人,后移居顺天(即北京)。其好友梁清标在其所辑刻崔子忠所绘《息影轩画谱》序中称崔子忠:“天启时为(顺天)府庠生,当生于万历年间。”又说他“甲申之变,走入土室而死”,当卒于1644年。周亮工记他“年五十病,几废之。后遭寇乱,潜避穷巷,无以给朝夕。有怜之而不以礼者,去而不就,遂夫妇先后死”,当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前后,根据《书画记》和《神州国光集》等史料著录,崔子忠的绘画作品涉及面很广,在人物、山水、花鸟方面都有涉及,但以人物的特长,与陈洪绶并称为“南陈北崔”。他作画用纸或绢素,没有定数,或为卷轴,为中幅册页,为扇面,似乎很随便。他的同代人孔尚任在《享金簿》中称:“莱阳崔子忠,号青蚓,人物称绝技。人欲得其画者,强之不肯。山斋佛壁则往往有焉。后竟以饿死。予得十八尊者一卷,笔意超迈,神气如生,每一尊者俱有自制小赞,字与画皆儒笔墨。”(见《美术丛书》第一集第七辑)。周亮工《书影择录》称:“画家工佛像者,近当以丁南羽、吴文中为第一,两君像一触目便觉悲悯之意,欲来接人,折算,衣纹、停分、形貌犹其次也。陈章侯、崔青蚓不是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遂,欲远追道子,近逾丁吴,若郑千里辈,一落笔便有匠气,不足重也。”(见《美术丛书》初集第四辑二三七页)崔子忠的书画,孔尚任推为“儒者笔墨”,而亮工以贬低丁南羽、吴文中、郑千里等人物画家,来提高陈、崔两家的绘画地位,虽有可值得商榷之处,但在明清以来以仿古为能画,笔笔讲出处,处处要师承,非某宗某派则为野狐禅,画坛了无生气,特别是山水画。自明董其昌画分南北宗,提倡文人画,至清代的四王、吴恽等,把山水画拔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相形之下,人物画是不被重视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看重陈老莲、崔子忠,并把他俩并称为“南陈北崔”,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画史上都说崔子忠“善画人物,规模顾、陆、阎、吴名迹,唐以下不复措手。白描设色能自出新意,与陈洪绶齐名,号南陈北崔”。这种评论是近乎实际的,他绘的《桐荫论道说法图》(亦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看题记,有可能误认为是陈洪绶画的。其好友梁清标在其死后为其辑刻的《息影轩画谱》,其人物造型、表现方法与陈洪绶的《水浒叶子》亦很相近。故有“南陈北崔”之说。他们两人在画风上相似,却不能相互代替,他们都以人物画为主要特长,社会声望也不分轩轾,但却各有特色。陈洪绶的作品才气横溢,寓美于形色,而崔子忠的作品却朴实无华,寓意于内蕴。按梁清标的说法,崔子忠晚年“息影深山,杜门却扫”浏览史籍,每遇有忠考奇节人物,义使巾帼英雄,绘图像,立传赞,虽称自娱,也可以起“顽廉懦立”,立德、立功、立言、立像,合称为四不朽之作。正因其作画极为注重立意,因此为当时的文人和画家们所推崇。崔子忠善于表达历史题材,尤其喜欢画文人们的风流韵事,他的《云中玉女图》、《苏轼留带图》、《桐荫博古图》、《临池图》以及罗汉道释等图,都是人物画,也都具有来历,题材不见得新鲜,但由于他构思画法有新意,或多或少加进自己的东西而成为新作,也是耐看的。《藏云图》即是此类典范,此图以人物为主,衬以山水,其高山大川的描写为刻画人物服务。由画中题识可知此画是为玄胤同宗所作,画中一团云气缭绕,是表现巫山浓云虚幻之处,“不辨草木,行出足下,生生袖中,旅行者不见前后。史称李青莲安平入地,负瓶瓿,而贮浓云,归来散之以内,日饮清泉卧白云,即此事也。”画面中唐代大诗人李白盘腿端坐四轮椭圆底盘车上,缓缓行于山路中。李白仰首凝视头顶上的云气,神态闲适潇洒;一稚童肩搭绳索,牵引车子,另一稚童肩荷竹杖,作引导状。在具体表现上,其衣纹作颤笔细描,虬折多变,折而不滞,颤而不散,突出了衣服质料的柔软质感和随风飘的动势,气意超迈,神色如生,可谓自成一家。
崔子忠不遗余力地颂扬历史上的隐逸君子,是其人生观的曲折表现,同时亦是明末文人们走投无路,徘徊苦闷的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其本人虽居于“京师”,身居闹市却过着清苦无为的生活,很有隐者之风,由于他缺乏陶渊明的生活条件,又不肯寄人篱下,侍奉新主,所以只有饿死。不识时宜,怀才不遇而又孤傲自恃,生不逢时,亦死得冤枉。
“孤傲绝俗”的评价,确实当之无愧,但以生命的结束为代价,其牺牲不可谓不大矣。历史上有伯夷、叔齐因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而崔子忠则因怀才不遇而又孤傲自恃,宁肯饿死,也不愿把画卖给不识货的庸人,宁肯病死在床榻上,也不愿意接受无礼者的援助,最终以自己的生命成就了李唐名作迥然不同的另一幅《采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