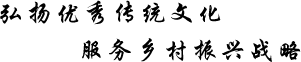目录
导言
安徽戏曲史方面除少量专著外,余皆散见于诸家曲论、笔记等文字中。涉及安徽戏曲者,省外主要有徐渭的《南词叙录》、汤显祖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王骥德的《曲律》、焦循的《花部农谭》、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严长明的《秦云撷英小谱》、欧阳予倩的《谈二黄戏》等;省内有潘之恒的《亘史》、程演生的《皖优谱》、陈澹然的《异伶传》、周明泰的《几礼居戏曲丛书》六种。当代有陆洪非的《黄梅戏源流》、完艺舟的《从拉魂腔到泗州戏》、刘永濂的《皖南花鼓戏初探》等书。除《皖优谱》在引论中以摘引形式,系统地组成了一个安徽戏曲小史纲,《黄梅戏源流》和《从拉魂腔到泗州戏》、《皖南花鼓戏初探》分别记述了黄梅戏、泗州戏和皖南花鼓戏的剧种史外,余皆以少量文字涉及安徽戏曲的历史。这些文字因是历史文献中难得见的戏曲记载,所以又都是弥足珍贵。有关安徽戏曲源流记载者有《南词叙录》中“称余姚腔者,则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证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前后,余姚腔盛行于安徽的池州和太平两府。又由《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之“至嘉靖而弋阳调绝,变为乐平、徽州、青阳”,及《曲律》之“数十年来,倡有弋阳、义乌、青阳、徽州、乐平诸腔出”等记载,可证青阳腔与弋阳腔、余姚腔的关系;他如《亘记》记载了明万历、天启时昆曲在安徽盛行,分成新安(徽州旧名)、皖上(安庆别名)两派;《花部农谭》记述了清初安庆梆子腔演出情况;《扬州画舫录》记载了清中叶花雅之争的“安庆有以二黄来者,而安庆色艺最优”;《几礼居戏曲丛书》六种,其中有近一半篇幅,记述了清道光以后几十年北京戏曲活动情况,徽班部分占了它很大篇幅。有关安徽戏曲声腔者有《秦云撷英小谱》论及吹腔之由来;《谈二黄戏》论述了二黄戏的演变过程。有关徽班艺人记载则为《皖优谱》和《异伶传》。 戏曲创作理论方面:向无专著,多散见于剧本的序、跋、凡例、评点及来往书信中,概括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追求进步意识,明确戏曲功能。明代休宁人程巨源,曾为徐士范刊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写过一篇序文。文仅500个字,题名《崔氏春秋序》,此文对《西厢记》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西厢记》作者王实甫、关汉卿都是“胜国名手”,在他们写的数十种作品中应以“此记为最”。他之所以这样评价,是因为他认为“人生于情”,爱情生活是人生的正当行为,是“愚夫愚妇”都“可以与知”的事。《西厢记》写自主婚姻也是有益于风教的。他对那些封建卫道士认为《西厢记》“导淫纵欲”是“不免呕喉”。他以《崔氏春秋序》作为《西厢记》序文的标名,也显示了他惊世骇俗的胆量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显然,程巨源的这种观点,在那个时代,无疑是非常进步的。晚明程羽文在《盛明杂剧序》中着重指出了戏曲的讽世的意义。他认为戏曲创作的本身就是鸣心中的不平:“才人韵士,其牢骚、抑郁、啼号、愤激之情,与夫慷慨、流连、诙谐、笑谑之态,拂拂于指尖而津津于笔底,不能直写而曲摹之,不能庄语而戏喻之”。这样,物感于外,情动于中,便产生了戏曲的生动形象,也才产生了“状忠孝而神钦;状奸佞而色骇;状困窭而心如灰;状荣显而肠似火;状蝉脱羽化,飘飘有凌云之思;状玉窃偷香,逐逐若随波之荡。可兴、可观、可惩、可劝,此皆才人韵士以游戏作佛事,现身而为说法”。这既道出了戏曲创作孕育、结果的过程,也指出戏曲形象对社会所产生的力量。清代包世臣在《书桃花扇传奇后》文中,把剧中的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这些市井小人物的形象,和那些晚明时期上层人士相比较,说是“备书香君之不肯徒死,而必达其诚,所以愧自经沟渎之流;柳敬亭、苏昆生艰难委曲以必济所得,而庸儒误国者无地可立于人世矣。”这番分析透露出了他对民族气节的尊重,对“抱忠义智勇、辱在涂泥”的小人物的同情,对辱国毁节的大官和名士们的蔑视。陈独秀以“三爱”笔名,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论戏曲》,他要求戏曲“要做得忠孝义烈,唱得激昂慷慨,真是于世道人心,大有益处”。并且指出“现在国势危急”,“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教师”,多写新戏,“无论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动,便是聋子也看得见,瞎子也听得见,这不是开通风气第一方便的法门吗?”这些论点,都是立足于戏曲应追求社会进步,弘扬民族精神。并且强调形象感受、潜移默化、陶冶性情是戏曲的功能。 安徽戏曲理论,一直是崇尚雅俗共赏,提倡当行本色。既重视戏曲观众的广泛性,也重视戏曲艺术独特的舞台性。清代歙县人张潮在《制曲枝语小引》中写道:“苟非当行,鲜有能道只字者”。也主张戏曲要“雅俗共赏,案上场上,无不可观”。清中叶另一位歙县人凌廷堪,他在《与程时斋论曲书》中也提出,如果不能驾驭戏曲的特殊创作规律,便“悍然下笔”,写成的作品便“惟谓之为曲则不可”。因为戏曲是“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故事”(明代程羽文《盛明杂剧序》中语)。它具有独特艺术形式和舞台一次过不可停顿的原因。 二是寻求创作规律,探讨发展途径。戏曲的题材处理,情节结构,人物描写,都受着戏曲形式的制约,都有着符合自身的特征。凌廷堪《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是最有理论价值的论曲诗。其中两首论元杂剧绝句的注语,一为“元人杂剧,事实多与史传乖迕,明其为戏也。后人不知,妄生穿凿,陋矣!”一为“元人关目,往往有极无理可笑者,盖其体例如此。近之作者,乃以无隙可指为贵,于是弥缝愈工,去之愈远”。这是凌氏论曲绝句中的重要理论建树,他认为“杂剧事实”不能与“史传”是否“乖迕”来要求,要“明其为戏”。正是因为是“戏”,那就允许作者对塑造形象作有益的虚构。他认为“若使硁征史传,元人格律逐飞蓬”。凌氏还指出,元人“关目”,往往有“极无理可笑”者,这也是元人杂剧本身的结构特性。因为,艺术逻辑与日常生活逻辑不同。戏剧的合理、真实,不能以生活原形作衡量,戏剧艺术本身具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相生相济,融为一体的特点,要求全“真”全“实”,结果一定是“弥缝愈工,去之愈远”。凌氏此一认识,非常深刻地揭示了戏曲的本质特征和创作的基本原则。这是中国艺术家长期实践的结果,是不可动摇的艺术原则。戏曲强调情节结构,最终还是为了人物形象能更加鲜明感人。张潮在《致黄官》中指出:“大抵传奇须分可演、可读二种,总以情节为主”。以后,清乾隆年间全椒人金兆燕在《重订昙花记传奇序》中反对“枝叶太繁,排场太板”。包世臣在《书桃花扇传奇后》中也强调要从全剧“属思铸局”。其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这和李渔的“独先结构”、“结构全部规模”、“头绪忌繁”等主张是一致的,这反映了清初戏曲理论界对戏曲情节结构的高度重视。 关于戏曲语言方面,程羽文在《盛明杂剧序》中指出戏曲要诠“情性之微”,也就是要揭示人物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这样才能“状忠孝而神钦,状奸佞而色骇”。张潮在《制曲枝语小引》也指出“世务人情,描写毕肖”,务必做到“婉转曲折”,极情尽致。和金兆燕同乡而又连襟的吴敬梓,在《玉剑缘传奇叙》中,对以爱情为题材的戏曲,认为应当写得“雕镂刻,畅所欲言,而后丝奋肉飞,令观者惊心骇目”。他说《玉剑缘》中的人物,如“铁汉之侠,鲍母子之挚,云娘之放”,都写得“尽态极妍”,令人难忘。 凌廷堪在戏曲语言上,崇尚质朴自然,通俗浅显。他《论曲绝句》第十一、二十四两首,高度赞扬了元无名氏《陈州粜米》杂剧的白描风格,元康进之《李逵负荆》杂剧语言的性格力量和绝妙神采。他还为另一首绝句加注说“‘半穷千里月,一枕五更风’,似晚唐人诗,于曲终不类也!”可见他反对那类工整、凝重而迂曲的“香词”。还明确指出诗词(是赋兴的)和戏曲(是塑造人物的)语言的不同风格。 安徽剧作家金芝,在《编剧丛谭》中,对戏曲的主题、舞台性、剧本的结构、合理性、克服戏剧冲突的雷同、人物关系的处理、语言与行动的关系等方面,都结合创作实际,作了较细致的分析,是我省唯一的一本论述戏剧创作的书。 戏曲表演方面:明歙县人潘之恒写的《鸾啸小品》,应算是一部有分量而又少见的戏曲表演理论专著。这是潘氏几十年戏曲的鉴赏录,对几代昆曲艺人的表演作了总结。他的理论不仅是开创性的,而且自成体系。戏曲艺术是剧作者、演员和导演集体创造的成果,这在潘之恒表演理论中是非常明确的。他在《情痴》一文,评述了徽州吴越石家班一次成功演出的经验。指出首先是汤显祖提供一个好的剧本,其次是“主人越石,博雅高流,先以名士训其义,续以词士合其词,复以通士标其式”,这样具体地完成了戏曲导演各个阶段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演员具有良好的素质,扮杜丽娘的江孺是“解杜丽娘之情人”,“能情者而后能写其情”。扮柳梦梅的昌孺也是这样,加上演出时能临场发挥得出色,便组成了这次成功的演出。 潘之恒重视剧本创作,他认为戏曲佳作“皆生于情”并且都是能将“情”达到“致”(顶点)之境地者。他更重视对演员艺术素质的培养。他认为一个好演员必须具备“才”(表演才华)、“慧”(领悟能力)、“致”(独特的表演风格)三方面条件。三者缺一不可。他写了《曲余》、《正字》、《叙曲》等篇,专门论述演员对唱曲如何处理。还在《与杨超超评剧五则》中总结了表演五要素“度、思、步、呼、叹”。在解释这五个表演技巧时,贯彻了“形神兼备”原则。“思”要得“捧心之妍”,“步”要防“神斯窘矣”,“呼”应有“凄然之韵”,“叹”须“其韵悠然”,而这几个方面的最佳状态,便是“度”,也就是“才、慧、致”的最大限度的发挥。可见,潘氏既有对形体和程式动作方面的要求,也有对神态、风韵方面的追求,既要求其形似,又追求神似。 潘氏主张表演风格多样,各类声腔演员应互相竞技,各擅其长,风格不同,同样值得称赞。他认为评价表演要能理解演员“分擅所长”,“才有殊长,何嫌媲美”。这种鼓励不同流派和风格的主张,是符合戏曲发展繁荣途径的。 潘之恒的戏曲表演论,是从舞台实践中总结,又回到演员中去,指导新的表演创作。这些见解,沟通了文人作者与表演者之间、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所以是可贵的。 早于潘氏100多年前的凤阳人朱权,在他的一部明初戏曲理论名著《太和正音谱》中,对声律、歌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了“先要明腔,后要识谱,审其音而作之”。他主张歌唱应“自然”、“融神”、“合人之性情”,反对“做作”、“轻薄”、“乱人之耳目”。潘之恒在他的表演论中,也写了《曲余》、《正字》等篇,专门论述了“调音”(处理歌唱)。他也强调“审音”的重要性。他细致地分析了“识曲”和“宣情”的关系。并指出首先要“正字”。“夫曲先正字,而后取音。字讹则意不真,音涩则态不极”。他对唱曲的声音效果,在音色的美好,节奏的准确,唱曲处理的恰到好处等方面,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体现了他们对戏曲艺术的严肃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