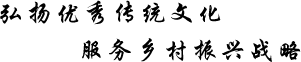第三十八章 修巨帙文人皆惊心 绝奢望痴官染痰疯
乾隆要在热河过冬,纪昀十月就奉旨回京筹办《四库全书》。他一回北京,立即召集礼部、翰林院、都察院、国子监全体阁僚大臣和各司堂官,连着十天会议,说明乾隆“稽古右文”的圣意,布置征书筹办事宜,下令各部除常规例行部务外,所有人员全部到文渊阁分检图书,又令奉天故宫、圆明园管事、内务府,速将文溯阁、文源阁和避暑山庄文津阁,将所有图书原封原装运往文渊阁,以备辑校。与会除了官员,还有一百余名致休文臣、京师直隶名流硕儒,所有翰林院的庶吉士、编修也都来“恭予盛事”。纪昀也真不畏烦难,白日主持会议,征求与会人意见,晚上就在军机章京房里写节略条陈及各种建议,一份上奏乾隆,一份发邸报,一份交誊本处,誊发十八行省所有督抚、提督、将军。每日只睡一两个时辰,饿了渴了就着点心到侍卫处吃胙肉,喝点茶就又去办事。乾隆虽然远在承德,却每天都有朱批圣谕给他,都是夜间写了,用八百里加紧,限午前送到纪昀手中,凭回执缴旨,除了每日送一枝人参过来,还特旨令太医院派三名御医轮流在纪昀跟前,有病医病,无病防病——自有清开国,皇帝待臣子如此优遇闻所未闻,那纪昀越发勤勉,连去东厕解手也是一溜碎步快走,见了熟人也都招手即了。直忙了一个月,各阁图书汇集,修书馆址、校阅誊录人等的办差规矩,乃至吃喝拉撒睡诸项事宜无不妥帖,又密密麻麻写了一份万言奏折,亲自誊录着人快送承德。此时,编纂《四库全书》的事已经成了轰动朝野的事。
“纪昀能办事,能吃能干能熬,十分难得!”乾隆接纪昀折子。当晚宿在钮祜禄氏房里,就着灯细细读了,用手抚着纸道:“累得走路都打瞌睡,还肯自己誊折子,字写得一笔不苟!可见其忠忱之情啊……”钮祜禄氏给他端来一大盘子哈密瓜,还有一盘子紫微微的葡萄,小心地用羹匙柄挑着瓜瓤,笑道:“那是皇上亲自选拔的人才,还错得了!不过我也听说他爱吸烟,喜欢作践人,像个能吃能喝的粗长工。如今主子待见他,听说见人都不大理睬,主子见他,还要提携教训才好……”乾隆正拈了一粒葡萄含在口里笑着听,见是这话,立时敛了笑容:“朕该怎样如何,自有朕的道理,这种事你还插口,不怕处分?纪昀这一个月办的事,换了别人一年也未必办下来。他累极了,礼数不周也是自然的。粗长工?那些不会用长工的才嫌长工吃得多呢!山东头号大业主吴老秀才招长工,第一关就是比吃烙饼,吃不进二斤干面烙饼的不收!”
他的话虽不疾言厉色,却说得郑重深沉。钮祜禄氏顿时脸一红,忙福一福,说道:“我说错了,那是女人见识。我是个有口无心的人,主子最知道我的,从不敢说政务。主子您得体恤我这没心眼的——不的下回纪公进宫,我隔帘儿给他蹲身赔不是,成么?”乾隆知道她生恐自己恼了拔脚去了,听她说得可怜兮兮,一笑说道:“你上他下,你满他汉,你女他男,背他说话,赔什么不是?历来后妃太监干政,没个不把政务弄得七颠八倒的,朕要听你方才的话,给纪昀没意思,不就错了?祖宗这个法则,就为防微杜渐——给朕磨墨,朕还要再坐一会儿,”钮祜禄氏顿时一颗心放下,双手捧过一方端砚,半侧着身子磨墨,乾隆见她怯生生的,也觉可笑,又笑道:“也有能吃不能干的,我在山东赈灾,见过吴老秀才开革的一个长工,一脚能把石滚踢得竖蜻蜒似的立起来,让他去割麦,还不抵一个十三岁的孩子。”钮祜禄氏笑道:“上回省亲回娘家,他姨姨家也有一个,是个大饭量儿,人家编了个口诀,说‘大肚汉,大肚汉,能吃不能干,一顿吃了两桶饭,挑了二斤半,压得直出汗——世界大了,什么样人都有呢!”
乾隆听了格地一笑,琢磨着这个口诀儿“能吃不能干……挑了二斤半,压得直出汗……”渐渐笑得浑身发抖,手中的茶杯也倾得半斜,说道:“这个词编得有趣!这样的臣子朕也不要一一笑出一身汗来,好轻松!”他站起身,两臂平伸,大大伸展一下,盘膝坐在炕上小卷案前,钮祜禄氏忙又跪着替他加一盏聚耀灯。在橘黄色明亮而柔和的灯光下,乾隆显得格外气定意收,拉过纪昀的奏折本子,在后边敬空处写道:
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记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藏书之人乎?若此番明切宣谕后。仍似从前畏疑,不肯将所藏书名开报,听地方官购借,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处,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此批誊清转张廷玉、鄂尔泰阅,即行明诏颁布天下周知。钦此!
写完在灯下又浏览一遍,满意地说道:“你这墨不但香,还带着宝色,字看去就精神多了。纪晓岚一笔好字,朕不能叫他暗笑了去。”想想,又提笔另拉一张纸,写道:
诸事既备,尔可稍事休息,至少不可少于三日。任事都不必去理他。劳乏过度,最易心血短缺失眠,所以要补些。着人赐些当归与你,鸡汤熬好,每晨服用。肤盼下次见尔,仍旧武人气概,灯下又及——长春居士从怀中取出一方小玺,铃上了,交给太监,说道:“叫傅恒过目,立刻发纪昀!”
次日上午辰时,明诏已到纪昀之手。皇帝关怀,情辞恳切,刚上一点乏意的纪昀立时又全无睡意,督着上书房、军机誊本处的吏员立即发往各省,因思两江浙闽等处民间图书最多,又赶着给尹继善写信.和着诏旨一同发出,自忙到大色断黑,嚼了一盘胙肉,喝了一杯酽茶,然后倒头便睡。顷刻之间军机章京房已是鼾声如雷。
五日后明发诏谕即到南京,尹继善当庭拜了黄匣子,打开诏文读了读就放在一边,叫人去请巡抚范时捷、布政使道尔吉过来议事,自己便拆看那信,信写得不长。前头报圣安,寒暄数语,后边切入正题:
兹事浩大,仆惟竭愚公之志耳,两江江浙人文之地,家有图书插架琳琅者不可胜计,散征民间版籍,正宜借重吾公。公原命赴两广之任,今上已有两番诏谕驳回部议,以资熟手。万不可存暂任之心,怠忽轻易,则必失圣望。惟征书一事,查借私藏,或靳矜惜爱,或畏惧后祸,此亦不易强索,惟以善言导之,规以圣意劝其慨借,善本宜购者以金赎,余皆以印信借据用后壁还。此亦清风俗正人心之大事,弟惟勉命从事,所虑者左右助力者乏人,仰兄留意体察人才,荐之库馆备用,匆匆无任感激。
看罢方折起页子,即见张秋明甩着步子进来,十分利落地向尹继善一躬又一揖,脸色又青又白。一丝笑容也没有,径自站在签押房当央,说道:“司里差事弄不下去了,请制台主持公道!”
“哦,弄不下去?”尹继善翻起袖里子,双手捧诏书小心翼翼放进匣子,又把信折起塞迸袖子,看也不看张秋明一眼,说道:“——所以你又来找我?如今你成了我的一块臭膏药了,贴上要寻我的事了?”张秋明冷笑道:“制台是江南王么!有您撑腰作对,下头人谁还听我的?您就要走的人了,横身儿和我们属下打别扭,这何苦呢?再说,‘一枝花’一案,是我臬司衙门主办.如今下面厅里的司员都径直向您汇报。把我这按察使倒撂在一边,今年刑部的案汇叫我怎么写?”
尹继善看着这位整日寻事的下属,半晌突然一笑,说道:“你天天来说‘一枝花’.其实当初这案子最早是交结你的,你没有理嘛!我忙极了,只想告诉你,你没有一个字说对了!这是总督衙门,所有江浙两省的军政、民政、财政、学政、法司,没有我不能管,没有我管不到的,你是听参的人,还是本分一点。晓得一点上下之礼。从明日起,我的戈什哈就要把你拦在仪门外——真奇怪,我怎么会选了你这么个人来作臬司,想起来就羞死了!”自从上次当众龃龉,这个张秋明突然变得疯了一样,三天两头来缠尹继善,有时连会都议不成,尹继善也只是耐着气儿冷冷打发他回去,今日第一次发作,连一句脏话也没有。却字字如刀似剑,若冰若霜,旁边站的戈什哈都听得心里发毛,张秋明也被他激得打个愣儿,说道:
“你——?你不见我?就是张衡臣,他敢说这话?”
“他不敢我敢!我立时要见巡抚,藩司们议事,你请驾吧!”
“我不走!你侮辱士大夫!我要辞职!”
“你就是这一套。我看你少来我这里,多去瞧瞧郎中,恐怕你有失心疯病儿。”尹继善冷笑着起身端茶一啜,拔脚就走,头也不回说道:“我到西花厅议事,张大人愿走好生送,愿留好生看茶,不许慢待。他有病!”众戈什哈一个个绷着脸暗笑,纷纷答应领命。张秋明气得癫子一样。口中叫着“你小尹才有病,你才发疯”!一边向外扑,早已被两个戈什哈架着拖回来,往椅子上一搡,道:“您大人安分着点,别叫我们作下人的难为!”
此时恰范时捷、道尔吉从仪门进来,后头还跟着刚从北京赶来的刘统勋、黄天霸,道尔吉前头先导,揖让着刘统勋进月洞门,听见这边嚷嚷,都偏过头来看。尹继善已走上花厅台阶,又回步来迎,笑道:“那是个官场失意、痰迷心窍、百药不入的人,理他做什么!前脚接傅六爷信,后脚延清你们就来了,好快的腿子!”刘统勋知他说的是张秋明,便随着走进花厅,落座接茶,说道:“在承德皇上召见,说起过这人。皇上说,隔山拜佛不敬佛,到他当宰相,无山可隔,就好当曹操了。把他贬到广州九品县丞待选,重新拜起!”说得众人都笑,尹继善见黄天霸垂手站着,指座儿道:“天霸已是天下第一名捕。还和我闹客气!”黄大霸才揖手斜签着坐在一边。
“纪晓岚这一次算是造起一个大声势,他大不易!”范时捷是个一喝茶就出汗的人,摘了大帽子揩着前额道:“不过我心里还是犯嘀咕,天下图书都收,都用车送北京,怕紫禁城也盛不下。还要看要删要改要校要编,那是多大一部四库全书?”刘统勋笑道:“那是你读圣谕读得不仔细。不是见书就收,是要珍版秘藏,不然,北京城腾空也盛不下。饶是这样,文渊阁里现在书堆得已经没有插脚地方了。”尹继善用扇背轻拍手心,莞尔一笑,说道:“这部书大得很了。我粗算过一笔帐,修编学者没有三百人,缮录人少了四千,没有二十年工夫此事办不下来!什么《永乐大典》,又是《古今图书集成》,比起来都成了这个——”他伸出小指甲掐了一下,又道:“不过咱们还说咱们的正经事吧。大霸,你见过这里巡捕厅江定一没有?”
黄天霸听他讲说,修一部书要费这么大精神气力,心里正惊讶嗟叹,被这位思绪敏捷的青年总督兜地一转问到了案子,怔了一下才道:“标下已经见过江头儿,还有马总头也见了。这个案子江头儿只打外围,真正进‘一枝花’风水地里趟的,全是退休的老衙役。当初离南京我还心里别扭,后来越看刘大人和尹大人的决断,真是人神不测!‘一枝花’现在燕子矶、老故宫、虎踞关和玄武湖北机房屯四处香堂,有香众约两千三百人上下,灵谷寺南屯旧五通庙处设有一座总堂,总堂管着全省十三处香堂,南京的四处只是代管,总共有在堂徒众一万四千名。敌情就是这样。”
“‘一技花’呢?刘统勋边听,目光游移不定,似乎在搜索着什么,问道,“这些香堂里都有我们布的眼线么?”黄大霸道:“总堂和南京各香堂都有。下面县里有的有,有的没有布线。有的县香堂只初一、十五聚半个时辰就散了,诡秘得很。燕人云再三打听。他也真费了心,‘一技花’似乎确实不在金陵了。他心绪很坏,找不到‘一技花’想自杀,也要防他访到‘一枝花’后通敌逃走,我两个太保跟着他就为防这一手。朱绍祖和梁富云都是精干人,失不了事的。”道尔吉己听过江定一汇报几次,略知案子头绪,便道:“像燕入云这样的,干脆补进你的太保里头,有功名系着他。就不会跳槽儿了。”黄天霸笑道:“爷不懂江湖里的事。十三太保变了十四太保就不香了。像燕人云。也是无可奈何才跟了我们,与其用功名诱,不如鼓动他报仇,杀胡印中来得实在。但也可用功名虚诱一下,我还想请示延清大人能否接见他一次?”刘统勋道:“我们就不用见了吧。待他立功之后再见如何?”
尹继善知道刘统勋是自矜身份,想想也有道理,又怕黄天霸失望,遂道:“不妨先季他一个千把总,且在你底下办差。待这案子有了眉目再见他不迟。他现在还是个没有身份的待罪囚徒,善听善见,于朝廷体面有损。”刘统勋道:“元长,照天霸方才说的,江南省匪情已经清楚,我看可以动手剿了。只是点点线线的太多,要一齐动手,一夜之间全部拔除,单靠巡捕厅是不成的。我看可以让天霸主持,驻江南各地绿营兵来一管带,会议一下,同一日动手,这样可免消息走漏。元长以为如何?”
“这个不必。”尹继善两个铁胡桃在手中刷刷地转着,沉吟道:“‘一枝花’在各地香堂原都有明摆着的,不过仗些邪道法术,或驱鬼逐狐,或跳神祛痰,哄着愚夫愚妇入会。这一万多人断不能按逆匪对待。不小心激出大变,反而更不美。我赞成全省同时行动,但最好不要开会,用我的令箭。咱们商量好了,某日某时同时发往各县,只叫驻军戒严待命。还由各县快捕去,只把各香堂为首的缉拿起来,出告示令其余入会人到官衙自省首告,他们摊子坏了,再窝里炮,没有个能再藏身作乱的。南京这几处声势可以大些,动一动兵助威,香堂里要紧徒众一体擒拿,然后取保待勘。不然监狱就挤不下了。”他拉开壁幕,口说手指,哪一处关防由哪一部行伍负责,何处关隘道路应如何设卡,都一一指示详明,笑道:“延清来信,我就想这事了。只要一开会就走漏风声,这种事要迅雷不及掩耳去作,又要持重有节,平平和和地办。太平了多少年,一下子各地大兵进宅,各城戒严,平空添些戾气出来。于人心不利。延清兄您看呢?”
刘统勋钦佩地看着这位气度雍容的总督。刚进中年的年纪,却早已开府建衙,十几年任方面大员,两代皇帝对他荣宠不退,笑道:“替你地方想得不周了,元长请谅解。这个策划我看无可挑剔。天霸,学着点,过去有个李卫。是缉盗总督,政治上肯采人言,自己却粗疏无学,无长这是从经书阅历里得的大道大学问,你不容易!”尹继善道:“身在此处,不得不然。江南是朝廷的粮库、钱库,又是人文盛地,要越太平越好。天霸,出力的事交给你了,延清公和我坐镇总督衙门,专等你的捷报。这个差使办好,我和延清合折保你个副将!”
“谢尹大人、刘大人抬爱垂青,刘大人的训诲标下都铭记在心里。永志不忘!”黄天霸又是感激又是佩服,更是激动,”黄某是一个开镖局走江湖的,能得二位大人如此知遇之恩,万刀加身不足为报!只是如此一办,标下深恐易瑛等人畏惧网罗远走高飞,将来缉捕不易。实是终生之憾!”“这个不要紧,”刘统勋目中幽幽闪着绿光,格格一笑,说道:“在承德我向皇上恳切地奏过。皇上说,‘稳住大局,拔掉江南大患,比什么都要紧,你拆了她的庙,她就得当走方和尚!世上事有的怕打草惊蛇,有的就要打草惊蛇!朕就要看这女人在这一朝能弄出什么名堂。朕要活的‘一枝花’,瞧她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妖精!她没有根子,充其量不过是个逃犯,哪个县的衙役都能办了她!’圣上有这旨意,我们可以放胆做去。”
几个人聆听乾隆的话,早已都站起身来,尹继善道:“圣虑高远!就照这旨意,咱们尽力而为。”刘统勋笑道:“你们还有事,我不再打扰了,和大霸我们回去合计一下,再来请你的令箭。”说罢辞出去,因见张秋明背着手仍在签押房里转悠,刘统勋招手叫过戈什哈.说道:“告诉张大人,尹继善留任南京总督,不去两广了。见面日子有着呢!请他回府,不要扰乱公务,实在想不开,到驿馆来见我刘统勋。”说罢向送行的尹继善一揖去了。尹继善也不理会困兽一样红着眼盯自己的张秋明。道尔吉打心底里腻味张秋明,一落座便道:“这种人在我们蒙古叫老牛皮筋,什么样的宝刀都切不断的,部落里出这么个痞子,老人们一商议就砍死喂鹰去了。和他客气什么,皇上有旨意叫他去当县丞,我明大就给他放个缺,挂牌子叫他滚蛋!”
“汉人也有叫痞子,或者叫滚刀肉。”尹继善绝不生气,摆手请二人坐,笑道:“器量也是本领,还是等着部里票拟来了再说。”范时捷道:“说怕他去寻刘统勋的不是,那太失金陵官场的体面。”尹继善道:“刘统勋一辈子专门对付这种人,刀下不知死了多少。他真敢去,未必能像我这么客气——咱们议一下征借典籍的事吧!”
范时捷吁了一口气,总督和巡抚不是上宪下属,总督偏于军政,巡抚则偏于民政,征集图书当然是他的差事。想了想,说道:“我自问才力,断然不及元长万一,所以还是唯你马首是瞻。征书已是天下皆知,但各省都还没动,一是借,是书主自己来报,还是官府去登门借,‘借’就有还,借据怎么打,谁打?借来书交给谁,又怎么交,将来怎么个‘还’法?有的是珍版,借要有押金,购要有购价,这书价怎么评。怎么量,银子从哪项开支?还有,哪些书征借,哪些书不征借,也都要有个细则章程,高低宽严都要得宜。这件事看似容易,办起来棘手烦难呢!”“老范说的是。”道尔吉道:“比如我,已经有信儿.票拟离任出缺。没有章程,连银子也不敢批,批了我再一走,就变成了亏空。有些书是很值钱的,卖到万金以上的宋版书我都见过,还有个古董鉴别的事儿,该由谁来办。我说心里话,制台不妨委员直接到藩司,专办这差使,要怎样我都没有说的。要依着我的本心,宁可等,等别的省,有了成例,我们也好办。”范时捷笑道:“老道怕亏空啊!现在早已有人闹起亏空来了,你担心个什么?”道尔吉道:“我也没那个担待,朝廷征书我来担亏空,也没这个理。”
“不要说笑了。”尹继善看看表,一笑即收,松快地透一口气,“征书其实是件极难的事,因为是‘借’,就有个两厢情愿的事,不能搜,不能抢,不能硬。可又不能软。不然没法向皇上交待。我同意等,等外头各省成例。但等也有个学问,是呆子等烧饼,傻看,还是搭棚子歇着凉儿等?方才说了许多许多的繁琐事,归根儿是要有人专管。我看,江浙两省各设一个局,就叫征借书局,各县一个支局,专差专办。叫他们慢慢琢磨章程,观看邻省有什么成例,再听朝廷有什么旨意,我们进退就缓松了。”
这个“进退缓松”的办法还没详加说明,范时捷和道尔吉都已透彻领略:这其实已经是个敢为天下先的行动。朝廷催省里,省里催局里,不催,不过养活几个闲人而已。办得好,自然督抚藩台受褒扬,办得不好,自也有地方委罪,两个人悟到这一层,一腔烦恼皆化作乌有,顿时都眉舒意展。这其中有“雷声大雨点小”的用意,更是彼此心照不宣,范时捷笑道:“罢罢,我是服了你了!明儿就办!”道尔吉道:“就请范中丞委员,我也委个副手。不过‘征借’名目嫌着硬些,不如叫个‘采访遗书总局’.下边叫支局或分局,听起来礼让温存些。”
“好,就叫采访遗书总局!”尹继善从谏如流,立时一口赞同,“这样办事就方便了。”他起身转悠着,只是手中团团转那铁胡桃,眯着眼仍在深思:采访遗书修四库全书,屡次诏书他都细细读过,“稽古右文”是文治第一事,能在里头有所建树,是文人莫大功德。但说“采访”,谈何容易!庄廷栊文字狱案是久远了,朱方旦邪说一案波及不广,也不去说。戴名世《南山集》一案才过去二十余年,一道旨意下来,三百余家文人祸从天降。雍正朝各派党争中文坛波起,又掀起汪景祺逆书一案,陆生楠诗案,钱名世谀颂年羹尧一案,查嗣庭诗案,更有吕留良、曾静、张熙,逆书逆案,轰动天下、震惊朝野。雍正帝亲自挥毫写十万余言〈〈大义觉述录〉〉颁布学宫,戮骨、斩首、凌迟动辄百数,侥幸活下来的钱名世,人虽兔死,被雍正赐匾“名教罪人”悬之族门,每逢初一、十五,地方官来检阅悬挂情形,这些事都是当今文人亲眼目睹,寒胆未温,如今又要征借,谁敢贸然“借书”给乾隆看?尹继善还有更深一层的忧虑:他自己也是著声海内的文人,江南风雅领袖,他的藏书楼里就有不少宋版秘籍。哪些该缴。哪些不该缴。一时也难决断,有些书不检阅一下违碍语,是绝不可交给这个纪昀的。深思良久良久,尹继善抽着冷气说道:“局子立起来,先请几位老夫子把我们大员们的存书先看阅一下。把没有忌讳的书先送上去。近人今人的著作尤要留意,有违碍言语的暂时一律不送。伤风败俗的书该查禁的也要这个局来办,文运关乎国家气数,也是盛世之风貌,我不愿江南官场出事情,也不愿文场出事情,要给皇上帮正忙,不要帮倒忙。”
范时捷和道尔吉虽然不知道这一刻间尹继善已动了这么多的念头,但从他沉甸甸的语气中隐隐觉得这件事分量极重,历来朝廷说话不算数,文网一张先诱后杀的例证范时捷见的比尹继善还多。
刘统勋回到驿馆,召集自己带来的随员和黄天霸的十三太保,就在总督衙门议决的事向下安排布署。要黄天霸主持详定破案规划,自己掌灯另坐一桌看当日从北京发来的廷寄内谕和邸报。先浏览邸报,说孙嘉淦和史贻直病重,己向乾隆上遗折,乾隆自热河派身边的御医星夜回京诊视,并带恩诏加意抚慰。又说纪昀回奏各省征借图书,奏请户部拨专项银款发省台资用,还有勒敏新到云南铜政司,各矿今年采矿炼铜比去年增加一成,有旨调十万斤精铜到南京铸造制钱,并命江西铁矿局拨精铁三十万斤,亦交南京藩司,为兵部铸二十门红衣大将军炮。又有刘统勋为黄天霸请功奏折,旨意着交部议……接着看傅恒发来的廷寄,恰黄天霸一干人正议破案日期,计算各地文书到达期限,众人七嘴八舌说得热闹,刘统勋不禁抬头看了看。黄天霸忙道:“大司寇,扰了您了,我们到耳房去。”
“不用了,不碍。这边还是机密些。”刘统勋无所谓地一摆手,“我插一句——本月二十六二十七都可,只要机密——谁泄露,无论有意无意,我刘某灭他九族!”说罢又拆看一个火漆通封书简,却是讷亲亲临刷经寺驻节大营,慰问大金川将士,会议来春进军计划,并请调拨过冬军衣、军被、油衣、皮靴、毡幕、砖瓦、柴炭、干菜,连锅碗瓢勺一干细物都开列成单奏上来。因见后边有朱批,刘统勋忙坐直了身子,看时却是:
转刘统勋一阅。讷亲差使终于上了手,朕甚喜甚慰,预备得把细些终归是好,金川此役宁可慢些,决不宜复蹈败辙。致朕蒙羞,讷亲尚可治乎?此件亦转尹继善看,采购之事由他办,钱从勒敏处调拔,刘统勋的军机帮办身分督他从速办理。另告,岳钟麒已移松潘,以川陕总督视事,归讷亲节制。钦此!
因见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忙戴上花镜细看,是乾隆蝇头小楷写着:
皇后亦甚惦记汝,赐貂裘一袭,行将弛送。你小主子要一件民间百衲衣,你可代主子娘娘留心物色。
刘统勋想起那年元宵节前富察娘娘特意赐自己鱼头豆腐汤的往事,心头一热,眼眶一红,忙又收摄心神,闭目思量着写回奏谢恩,又想着孙嘉淦、史贻直同气之情,也要写信带进京去。正打腹稿,驿丞已掌上灯来,众人忙都住口,那驿丞一手提壶,往各灯盏里添油,口中道:“张臬台来了一会子了,坐在门房里不走,说刘大人召他来的。大人们都还没吃饭,要不要稍歇一会,见见张大人?我看他有点神不守舍的神色……”刘统勋立时勃然大怒,腾地红了脸拍案而起,却又按捺住了,说道:
“西耳房见他!”
驿丞答应着出去。刘统勋交待众人:“按方才分的差使,拉开摊子各自拟出细则。回头交我看。”一提袍角便出来,径到西耳房来。却也不肯失礼,铁青着脸,阴沉沉吩咐上茶,问道:“老兄夤夜枉驾,有什么事体?”说着,灯下细审张秋明脸色,只见他颊上薄晕潮红,目光呆滞如醉,顾盼间头摇身动,仿佛头重脚轻的模样,遂问道:“老兄是刚吃过酒么?”“不不不,没有没有!”张秋明一惊一乍说道,“卑职从不吃酒的,从不吃酒的!尹继善才是最爱吃酒,还有范时捷、道尔吉,不但吃酒,而且看戏。南京的名角他们请遍了,有时在石头城那边,有时在莫愁湖——长江岸燕子矶一带也常去!”刘统勋万不料他如此饶舌,听他还要继续说尹继善“吃酒”,辩解自己不吃酒,不耐烦地问道:“你来见我,就为说尹元长吃酒?”
“对,啊不!”张秋明闪着眼道:“我听说大人叫我来的,来会议‘一枝花’的案子!”
“谁告诉你我要议这案子?”刘统勋陡起惊觉。
“你呀你呀!”张秋明放肆地指着刘统勋的鼻子怪声大笑。笑得刘统勋身上起森儿,下意识地摸一把鼻子。张秋明更是笑得弯了腰,吭吭地咳着,又道:“你还是个当世包公!忘了我是臬台,比皇上忘性还大呢——我来告诉你,臬司就是按察使,按察使就是管这一省刑名案子的……”
刘统勋早已起了疑心,见他眼睛又白又亮,兴奋得直喘气,口边说得白沫流出,料知是失心疯,又是恶心,又有些怜悯他,遂道:“请你回去,寻个郎中瞧瞧吧。少想差使,少想官场是非,心静下来就好了。”“大人这话不对了!”张秋明道:“我吃着俸禄,怎么能不想差使,怎么能怕是非呢?尹继善,哼,别人怕他,我不怕!我早就认得他,盯住他了,江南的银子垛成山,他能干净?我都记在小册子上头!刘大人,我要请你看册子。咱们——”他诡秘地左右看看,“咱们一道儿上折子,弹掉他,你就是第一臣,我是第二臣!咱们共保龙主!”刘统勋本还有点可怜他的心思,听他行为如此卑污不堪,倒觉自己愚得可笑,和个疯子坐地理论谈心。正思考应付办法,如果顶着,越顶他越上劲儿,不如吓唬他,连吓带哄送鬼出门为妙,遂格地一笑,说道:“你果真有心计,登龙升官有术!傅六爷有信儿,要调你军机处当军机大臣呢!家里要是有图书,你可要小心捡看一下,防着有违碍忌讳的,叫尹继善抓住把柄,什么军机大臣,也就泡汤儿了!”黄天霸那边的人都支耳朵听着,刘统勋如此严肃的人也能这样捣鬼,都不禁暗笑。
“好!我要当军机大臣罗!”张秋明一跳老高,连窜带蹦出院往外跑,双手张着叫:“军机大臣就是宰相!我和张廷玉一样了!——违碍不违碍,我都一火烧了!啊……哈哈哈……”
他像跳独脚高跷似地一纵一窜,消失在黑乎乎的夜幕中。远远还听他在暗中高叫:“尹继善!你等着瞧……我这就把你削掉,拔你的花翎,剥你的黄马褂!哈哈……”
“猪……”刘统勋咕哝一句,回到了上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