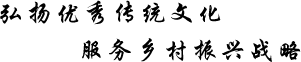第一百二十四回 挡剑锋草鞋著异迹 烧头发铁匣建奇勋
话说赵五听见赛半仙一句话就把他的心事道破,知道是要去报十年深仇的,心中不免着实有些吃惊。暗想:这倒怪了!难道连这些事情,都在相上可以瞧得出来么?忙向赛半仙问道:“怎么连一个人要去报仇不报仇,也都上了相么?而且报仇即说报仇便了,怎么连十年的深仇,又都瞧得出来呢?”赛半仙笑道:“这一半果然是在相上可以瞧得出,一半也是由我推测而得的。阁下目有怒睛,筋有紫纹,这在相上,明明已露出是急切的要和人家去拚一个你死我活的。一个人要急切的去和人家拚个你死我活,这除了要报宿仇,还有什么事悄呢?至于一口就说定你所要去报的,是十年的深仇,骤听之下,似乎有些奇怪,其实也是很容易解释的。大凡两下结了深仇之后,口头上所常说到的,不是三年后再见面,五年后再见面,定是十年后再见面。至于约到二十年三十年以后,那是绝无仅有的了。因为人寿几何,十年内的事尚不能知,如今竟欲预计到十年以外,不足成了傻瓜么?然观阁下急于要报仇的心,虽是完全显露在外面,一点不能遏抑,一方面却依旧很有忍耐心。这只要瞧你刚才对待那班地棍的神气,就可知道了,于此可知你所要报的仇,决不是三年的或是五年的,而定是十年的。现在十年之期已届,欲得仇人而甘心。所以在眉宇间,不知不觉的有一股杀气透露出来呢。”
赵五道:“尊论妙极。达不但是论相,简直是有一双神秘的眼睛,直瞧到我心的深处,把我秘密的心事完全都瞧了一个透呢。但是你说我此去性命不保,又是何所据而云然?难道印堂暗滞,真与人的一生有关么?”赛半仙道:“怎么没有关系。象你这样的印堂暗滞,主眼前就要遭受绝大的灾殃。而你此行是去报仇的,是去和人家拚一个你死我活的,这那里还有性命可保呢。”赵五道:“但还有一说:就算我此去性命要保不牢,然而倘能把仇人杀死,我也就十分甘心情愿了。请你再替我相一相,我此去究竟也能把仇人杀死么?”赛半仙连连把头摇着道:“大难,大难。照尊相看来:万事都无希望,那里还能把仇人杀死呢。这一定是仇人的本领强过于你,所以你的性命要丧在他手中了。”赵五道:“如此说来,我此仇是不能去报了。可是我为了此事,已费下十年的苦工夫,怎能为了你这句话,就此甘心不去呢?”言下颇露着十分踌躇的样子。旋又毅然的说道:“我志已决,无论如何,此仇我一定是要去报的,就是真的把性命丧却,也是命中注定如此,一点没有什么懊悔呢。”
赛半仙瞧见他这种慷慨激昂的神气,倒又把拇指一竖,肃然起敬的说道:“你真不愧是个好男儿。而且你是有大恩于我的,我如今如果不替你想个解救的方法,坐视你趋近绝地,这在心上如何说得过去呢。也罢,我现在也顾不得我师傅的教训,只好多管一下闲事了。”说着,即从身上取出一只很小的铁匣子,拿来递给赵五,并很郑重的说道:“恩公,你且把这铁匣佩在身边,片刻不要相离,将来自有妙用,定可逢凶化吉。”赵五见他说得这般郑重,倒也有些惊奇。但是细向这铁匣一瞧时,也只是顽铁制成很寻常的一只匣于,并瞧不出什么奇异的地方来。只匣盖紧紧阖上,宛如天衣无缝,找不出一些隙处,与别的匣子微有不同罢了。便又笑着问道:“这匣子究是作什么用的?怎么佩带了它,竟会逢凶化吉呢?”赛半仙道,天机不可泄漏,恩公也不必多问,只要紧记着我的说话,把它佩在身上,片刻不要相离,到了危难之时,自能得他之助。好在这匣子是很小很小的,带在身上一点不累赘。这于恩公,大概总是有益无损的罢?”赵五听厂这话,也就向他谢了一声,把这铁匣佩在身上。随即辞别了赛半仙,自向湖南进发。
晓行夜宿,不止一日?早已到了长沙城内。他的第一桩要事,当然就是如何前去报仇。便又自己和自己商量道:我当时约他十年后再见,在我果然时时刻刻不忘记这句活,在他想来也不会忘记的。如今十年已届,他如果还没有死,一定是在那里盼望着我去践约了。我倘然很正式的前去会见他,恐怕要有不利,说不定他已约好了许多好手,做他的帮手呢。那么,还不如在黑夜之中,冷不防的走了去,用飞剑取了他的性命罢。只要他一死,我的大仇也就算报成了。”继而又把头连摇几摇,暗道:“不行,不行!这算不得是大丈夫的行为。我如果只要暗取他的性命,那在这十年之中,那一天不能干成这桩事,又何必枉费这十年的苦工夫呢?现在我已决定了:他从前既是当着众人把我打败的,我如今也要当着众人把他打败,才算报了此仇。”主意既定,当下向人家打听清楚了余八叔所住的地方,即直奔那边面来。
到了余宅门前,并不就走进去,却先把余宅的左邻右舍和住在附近一带的人,一齐都邀了来。赵五便居中一立,朗声说道:“我就是十年前替湘阴人掉舞龙珠的赵五,不幸披这里的余八叔赤手空拳剪断了我的龙珠,使我裁了一个大筋斗,我当时曾说过十年后再见的一句话,诸位中年纪长一些的,大概都还记得这件事罢?现在十年之期已届,我是特地遵守这句约言,前来找着他的。此刻请诸位来,并不为别的事,只烦诸位做一个证人,使诸位知道我赵五也是一个慷爽的男子,对于自己的约言很能遵守的。此番能把余八叔打败,果然是我的大幸。就是不幸而再打败在他手中,或者甚至于性命不保,我也是死而无怨的啊。”这番话一说,大家不禁纷纷议论起来,无非又回忆到谈论到十年前,长沙人同湘阴人比赛龙灯的那件事.当下对于赵五此来,也有称他是好汉的举动的,也有骂他是无赖的行为的,毁誉颇不一致。
良久,良久,又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者,好象在这一方算是齿德最尊的,忽地在众中走了出来,和赵五打了一个招呼,颤巍巍的说道:“阁下此举,可算得是一种英雄好汉的举动,我们十分敬佩,决不敢说你是不正当的。不过兄弟还有一句话要对阁下说,阁下此次前来报仇,想来是要和余八叔个对个见个雌雄的。然而不幸之至,照现在的形势瞧起来,余八叔巳不能和你个对个较手的了。这在阁下新从远方到来,大概还没有知道这番情形罢?”赵五听了这话,倒好似游子远方,乍听到父母仙游噩耗这般的堆过,眼睛中几乎要挂下眼泪来。便很惊讶的问道:“怎么,余八叔难道已经死了么?难道他已不在人世了么,如果真是如此,我这个仇可报不成了。”
那老者道:“他死虽汉有死,但也与死了的无异。他在十三年之前,突然得了瘫痪之症,终日坐床不起。这不是已不能个对个和你较手了么?,赵五沉吟道:“果真有这等事么?”跟着又眼光一闪,很坚决的说道:“不要说他还没有死,只是瘫痪在床,就是真的死了,我也要亲奠棺前,和他的遗体较量一下的。而且他瘫痪在床,也只是从你们的口中说来,我并没有亲眼瞧见。说不定是他怕我前来报仇,故意装出这种样子来的,我倒不愿上他的当咧。如今我总得亲自去瞧他一瞧。至于较手不较手,留待临时再定,也无不可。”
他正说到这里,便另外又有几个人出来,向他说道:“余八叔的瘫痪在床.倒是千真万真,并不是假造出来的。现有我们几个人愿作保证,大概你总可相信得过。不过他既瘫痪在床了,你就是进去瞧他,也没有什么益处,你是好好的一个人,难道好意思和一个瘫在床上的人较手么?胜败且不必去说他,这种事情传说出去,于你的声名上很有些不好听呢,所以依我们之劝,你只当余八叔已死便是,也不必再报此仇了。至于你远道而来,或者缺少盘费,那我们瞧在你的侠义分上,倒也情愿量力馈送的呢。”赵五听他们如此说,倒又把两目一睁,动起怒来道:“这是什么话!我是报仇来的,并不是打秋风来的,要你们馈送什么盘费呢。如今实对你们说罢,不管余八叔是真的瘫痪在床,或是假的瘫痪在床,我总要亲自前去瞧一眼。如果只凭着你们几句话,就轻轻易易打消了报仇的意思,那是无沦如何办不到的。”
正在难于解决的当儿,余家的人也早被他惊动了。即有余八叔十三四岁的一个侄儿子,走来问道:“你这位客人,就是那年为了掉龙灯的事,和我叔父有十年后再会的约那一位么?如今来得大好,我的叔父这一阵子可天天的盼望你到来呢。只是他老人家患着疯瘫,不克起床,不能亲自出来迎接,特地叫我做上一个代表,请你到他的卧室中会上一会。你大概总可原谅他罢?”众人听了这—番伶俐的口齿,暗中都是十分称赞。而对于余八叔并不知道自己是个瘫子,居然还念着这个旧约,又居然邀赵五到他的卧室中去相会,一点不肯示弱,更是十分称奇,正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倒又不等赵五开口,不约丽同的,先向这孩子问道:“这些话果真是你叔父叫你来说的么?你并没有弄错一点么?”那孩子笑道:“这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我那里会得弄错。”随又回首向赵五说道:“客人,你就随我进去,好么?”赵五连连点头道:“好极,好极!原来他有这般的胆量,我还疑心他是装着疯瘫,故意不肯见我呢。”当下即跟着那个孩子,坦然走入余家。那班邻舍乡里,有几个是很好事的,为好奇心所鼓动,也就哄然跟随在后面。
余家的屋子,只是乡间的款式,并不十分深广。不一会,大家已都走入余八叔的那间卧室中。只见余八叔攲坐在床上,面色很是憔悴,一望而知他是有病在身的。不过手上还执着一只草鞋,正在那里织着,似乎藉此消磨病中的光阴呢。
一见众人走入室来,立刻停了手中的工作,把身子略略一欠,算是向众人致意。随又向赵五望了一眼,含笑说道:“你真是—个信人,说是十年后再会,果然到了十年,竟会不远千里,前来践约了。所可惜的,我在三年之前,患上了这个不生不死的瘫痪症,至今未能起床,巳不是一个健全的人,万万不能和你个对个周旋了,这可如何是好呢?”赵五听了这话,只冷笑上一声道:“照你说来,为了你瘫痪在床上,我只好把前约取消了么?未免把事情瞧得太轻易了。那我在这十年之中,为了立志报仇而所吃到的种种苦处,又向何人取偿呢?咳,老实说罢,这种丧气的话,这种没种的话,只有你们湖南人说得出口,我们山东人是无论到了如何地步,也没有脸说这种话的。如今还是请你收了回去,免得不但坍你自己的台,还要坍全体湖南人的台呢。”
这活一说,余八叔两个黯淡无神的眼珠,也不知不觉的微微闪动了一下,却依旧忍着,一口气说道:“哦,你们山东人决计不会说这种没种的话么?要我把它收回么?那我倒要请教你们山东人一声,如果你们易处了我的地位,究竟又应该怎样呢?”赵五一点不迟疑的回答道,“这还用问!如果是我,不但是我,凡是我们山东人,倘然有人寻上门来,要报深仇宿怨,只要有一丝气在,不论是断了膀臂,或是折了足胫,一定要挣扎着和那人决战一场的,那里会象你这们的退缩不前呢。”
余八叔被他这们一激动,实在忍耐不住了,又把两眼一闪劝,毅然的说道:“不错。我还有一口气在,并不曾死了去,决计不能退缩不前的。如今你要如何的比武,我就如何的比武,一切听你吩咐就是了。”这时和余八叔同个地方居住,前来瞧看热闹的人,倒又有些不服气起来,忙向赵五说道:“你这话看去好象说得很对。但是他瘫痪在床上不能行动,已有三年之久,这是谁都知道的。如今你逼他和你比武,他虽无可奈何已是允许了,但在实际上,请问如何能办得到?这还不如教他闭目仰卧在床上,索性静等你结果他的性命,倒来得直截了当一些,用得着说什么比武不比武的话呢。刚才你骂我们湖南人太投种,我们湖南人虽然不敢承认,现在我们湖南人倒也要还敬一声,说你们山东人太残忍一点了。”
赵五一听这话,气得两眼圆睁,怒声说道:“这是我和姓余的两个人的事,我提出要比武,他也巳慨然允许了。这于大体上巳没有什么问题,用不着你们旁人出来干涉的。如今我所要烦劳你们诸位的,只不过要请你们在场做个证人,此番不论谁生谁死,十年后再见的这句话,我们总算已经履行了。”他正说到这里,忽又象想到了一件什么事,怒意立时全消,微微笑了一笑,便又接续着说道:“而且我虽说要和他比武,却并不要强迫他起立。他既瘫痪在床上不能行动,就让他瘫痪在床上也是不妨的,因为我所决定的一种比武方法,很是变通,又很简单,只要我把两柄飞剑向他飞去,他能将这两柄飞剑完全挡住,就算完了事了。至于轮到他来出手,任他出什么新鲜主意,我是一点不敢推却的。这不是于他的能行动不能行动上,毫无一点关系么?现在请你们想想:我们山东人的生性,到底还是残忍,还是不残忍呢?”他把这番话一说,众人倒只好面面相觑,再也不能出来干涉了。
余八叔却早巳有些忍耐不住,便大声说道:“你既远道而来,当然,总要有个交代,不能一无所为而去的,又何必多说这些闲话呢。现在你所提出的这个办法,的确很是变通,又很能替我顾到,我那有反对之理?现在就请你把飞剑请出来罢,不要说只是两柄飞剑了,就是十柄百柄飞剑,我姓余的也是甘愿受的。不过闲人在这室中,恐怕要受惊吓,未免有些不便,还是请他们赶快出去罢。”这一个条件,赵五倒是听了十分满意的。因为照他的意思想来,在这些闲人中,难保不有几个有本领的人在内。他们当然是偏于余八叔一方的,倘遇危急的时候,说不定要出来帮助余八叔,那无论如何,于他自己总有几分不利了。现在把他们一齐撵了出去,他尽可安心行事。那余八叔的性命,差不多已有一大半落在他的手中呢。忙把头点上几点,表示赞成的意思道:“这话不错。这间房子并不大,我们比武的时候,再放些闲人在内,的确很是不便的,还不如先请他们出去罢。”说完这话,即把两眼望着众人,似乎向他们下着逐客之令。众人都怀着好奇的眼光而来,如今两人快要比武,好似锣鼓已响,好戏快要开场了,原舍不得离开这戏场而去的。不过这个条件,并不是赵五提出,却是余八叔提出的。他究竟是屋主人,他们违拗不得,只好怏怏然退出室中,但依旧舍不得不偷看一下,便相率转至廊下,就那疏疏的窗隙中偷窥着。
赵五却不知已在什么时候,在他身边的一只小匣中,把那一对飞剑一齐请出来了,众人只见他把口略略一动,似乎对余八叔说道:“你准备着罢。”即有一件东西,倏的从他口内冲出,化成一道白光,箭也似地一般快,直向余八叔的帐内射去。众人并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不过忖度起来,大概就是他所说的飞剑了。倒着实有些替余八叔担心,暗道:象这样夭矫无伦的东西,简直和游龙没有两样,很带上—点妖气,那里是什么飞剑,余八叔虽有绝大的本领,也只是一个凡人,又是瘫痪在床的,哪里抵御得来,怕不立刻就要丧在他的手中么。
可是众人虽这般的替余八叔担着心,余八叔自己却是十分镇定,昂着头望着那道白光,只是微微的笑。那种从容不迫的神气,如果被不知他正在和人家比武的人瞧见,还疑心他是在那里瞧看把戏呢。一刹那间,那道白光却早巳益行益近,和他的身体相距只有数寸了。他方把手中没有织完的那只草鞋,略略向上一举。只轻轻的一拨间,那道白光好象受了重大的创痛,再也不能支持了。立刻拨转身子,依着空中原来的路线,飞快的逃了回去。接着就悭的一声,堕在地上。而且奇怪得很,恰恰不偏不倚,正落在赵五的足边咧。这时在窗外偷看的人,再也忍耐不住了,便一片声的叫起好来。
这一来,可真把赵五羞得万分,急得万分,恨不得立刻把余八叔和那些窗外偷看的人,一齐剁成了肉酱。于是又把牙齿紧紧的一咬,低低的说道:“算你有有耐,这第一剑居然被你躲过了。但是这第二剑,我更当加上一些功劲,看你还能抵御得住抵御不住!”他一壁低低的说,一又把鼻子向内吸了几吸,两颊鼓了几鼓,好象正在练气似的。一会儿,把嘴尽量的一张,便又有一道白光,从他口内直冲而出。那夭矫的姿势,飞行的速率,比前更要增加了。再瞧那余八叔时,似乎也知道这一剑不比寻常,略略有上一种严重的态度,不比以前这般的从容不迫了。众人不免又替余八叔担着心事,暗道:不妙,不妙!看来这剑来势非轻,说不定余八叔的性命,就要葬送在这一剑之中了。否则,他何以也陡然变了样子呢?
说时迟,那时快,那道白光却早巳到了余八叔的跟前。余八叔忙又举起草鞋去拨时,这白光却果然和以前飞来的那一道大不相同了,好似在空中生了根一般,一点也拨移不动。而且不但拨移不动,就是这种相持不下的形势,看去也只是暂时的,不久就要失了抵御的能力,被这白光攻打过来,只要这白光在他的颈上一绕,他立刻便身首异处了。这时不但是余八叔暗暗叫苦,连窗下偷看的人,也都惊叫起来。这一叫,倒又使余八叔忘了自己是瘫痪在床的,也不懂得什么叫做痛苦,马上再把全身的气运上一运。说也奇怪:经不得他这们一运气,那只草鞋上立刻就象加增了几千万斤的气力,同时便不由自主的,又把这草鞋轻轻向前移上几移。这一移动不打紧,这白光可又受了创痛,再也不能在原处停留了,便和先前一样又飞也似的逃了回去。可是作怪得紧,这一次打的倒车,形势似乎比前更是紧张,等得退到了赵五的跟前,并不堕落下来,余势还是很猛,似乎要直取他的脑部咧。赵五这一惊真非同小可,不禁喊上一声哎呀,一壁忙又把身子躲了开去。总算运气还好,居然被他躲过了这道白光,只听得铿的一声,这白光又化成一柄短剑,堕在地上了。
谁知正在这惊喘甫定的当儿,又有一件东西,来势很是凶猛的,向他劈面打了来,定睛一看,不是余八叔手中的那只草鞋,又是什么呢?他起初对于余八叔的那只草鞋,原只看作无足轻重的一件东西,现在却已两次被挫,领教过他的本领了。暗想:我刚才仗着两柄夭矫无比的飞剑,还是弄他不过,被他打败下来。如今飞剑巳打落在地了,只剩着赤手空拳,那里抵敌得来呢。罢,罢,罢,光棍不吃眼前亏,不如赶快逃走了罢。至于报仇的事,不妨随后再诀呢。他一壁这们的想,一壁早巳搭转身子,向外便跑。这一跑,倒又使旁观的人哗笑起来,并不约而同的说道:“山东人好不丢脸,怎么就跑了呢?还敢说我们湖南人没种么?”
赵五这时逃命要紧,对于这种冷嘲热骂,也不暇去管得。只是这只草鞋好象有眼似的,依旧紧紧的跟随在后,不肯放松一点,眼见得就要赶上他了。而且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偶向肩后一看,余八叔不知在何时立了起来,已不瘫坐在床上了,也象要立刻赶了来。在这情急万分的当儿,陡的一个念头,倒又冲上了他的脑际,暗道:这赛半仙真和神仙差不多,预知我此行定要失败的。现在不是已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候么?不管他究竟灵验不灵验,不如取出他给我的那只铁匣来挡一挡,终比束手待毙好一点呢。他想到这里,早把那只小小的铁匣,从身边取出。也不暇回过身来了,就将那铁匣在肩后晃动了几下。
说也奇怪:他只晃了这几晃,立刻即听得轰的一声,好象什么东西炸裂似的。跟着便有一道青光,在火星飞溅中直穿而出,径向那草鞋打去:这时那草鞋便立刻现着屈服的样子了,忙向后面退缩,青光却紧紧追随不释。不一会,早巳追到了余八叔所立的地方。草鞋象已无地可避,要找一个地洞钻下去的,即听得嗒的一声,掉在地上。那青光骤然失了目的物,便向余八叔头上直扑。一时间,头发着火,竟蓬蓬然烧起来了。这一下,可把旁观的人一齐骇个半死,又不由自主的惊叫起来。但在这惊叫声中,可又变了一个局面了。只见一柄大扇子,陡的又从外面飞了进来,不消在上面扇得三扇,早巳烟消火灭,不但是余八叔的头发上停止了燃烧,连这青光都不知去向了。
众人正在惊诧之间,忽听得外面又起了一片笑声。忙争着走去瞧看时,却不知从那里走来了一位老和尚,脸上满笼着慈祥之气,一见就知是极有道行的。正望着那呆若木鸡的赵五,笑迷迷的说道:“赵居士,你立志定要报仇,十年有如一日,这是很可使人起敬的。不过遇见了一个瘫在床上的人,还不生上一点矜怜的心思,改变一下自己的宗旨,这未免太残忍一些了。至于那只铁匣,并不关你的事,我也不来怪你。只是我如果迟来一步,我的徒弟可就要送在你的手中了。”赵五听了,依旧木木然立着,没有什么回答。老和尚便又笑着说道:“但有一件事,倒也要感谢你的。我的徒弟被你这们一逼,在运气的时候,无意中把他从前所运岔的一口气复了过来。三年未愈的瘫痪病,竟从此霍然了。这不是很可喜的一件事情么?”赵五至是,才瞪着两眼,问上一句道:“如此说来,你莫非是无住和尚么?”欲知老和尚如何回答?且待第一百二十五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