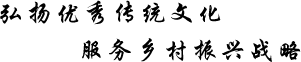第一百五十七回 壁上留诗藏头露尾 筵前较技斗角钩心
话说柳迟走至床头,向着高高悬挂着的那件外衣中一探,不觉失声叫了一句:“啊呀!”你道这是什么缘故?原来少年给他作为信物的那个碧玉搬指,竟已不翼而飞了。只是叫了一句啊呀之后,忽又似有上了一个转念,脸色间倒又扬扬如常,向少年说道:“如今你老兄既已到来,介绍一层,是不生问题的了。失去搬指与不失去搬指,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不过这碧玉搬指值价也不值价?失去了有没有什么关系?而我对于你交给我的东西,不知好好的保存,竟让他丢失了去,这当然是十分抱歉的。”说完,又向那少年的脸上一望。这倒是出他意料之外的,那少年的脸上,这时候满露着一派不快乐的神气呢。照他的心中想来,这少年是很有几分的侠气的,凡有侠气的人,对于义气为重,珍宝财帛为轻,这碧玉搬指不论是怎样的值价,然既已丢失了,至多不过想上一个如何把他追回来的方法,万不会也象一般平凡的人,把这不快乐的神气,完全放在脸上啊。
正在暗诧之间,又听那少年回答道:“介绍一层,当然不成问题。但这碧玉搬指,是先父唯一的遗物,一旦丢失了去,实在有点放置不下呢。而且,此中还另外有上一个关系,更不能听他随随便便的失了去,而不一加追问的。”说到这里,他的老毛病又发作,好同姑娘们怕羞一般,一个嫩颊之上,又瑟的晕红起来了。柳迟不免有点怀疑,正想追同一句:“所谓另外的一个关系,究竟又是怎样的一件事?”却已听那少年接着说下去道:“唉,这个贼人真可恶。别的东西一件也不偷,偏偏要把这个碧玉搬指偷了去。这显然的不但存上有一种深意,并连这个搬指的历史和另外的一个关系,也都知道得明明白白的。但我决不让他有这般的便宜,不论遭到如何的困难,我定要把这原物追回来。也罢,我们如今且先去见了黎一姑再说,大概她也已回到寨中来了。”
正说时,一线曙光,已从窗外透射进来。面在这曙光之下,又使他们在壁上瞥见了一件东西,无疑的,便是这大胆的贼人留下来的,倒使他们更把惊骇之情扩大起来。原来是一张小柬,上面是这样的写道:“人冒我名,我盗其宝。试一思之,真堪绝倒。只苦美人,毫不知道。欲返原珍,南山有堡。”他们二人瞧了这一纸小柬后,倒不免各人都上起各人的心事来。在柳迟的这方面,不觉暗叫一声:“啊呀,原来这来盗碧玉搬指者,便是白马山所延请的不知姓名的那一位能人。
他连我的冒名顶替都知道了,只不知他对于这节事的始末情形,已否完全知道?倘然他不知道我的冒名顶替,是出于将错就错,而疑心我是有意如此的,那可有些糟糕了。而在那少年一方面,也不觉暗唤一声:“惭愧,什么美人不美人,真是十二分的刺眼,大概对于我的事情,这个人已是完全知道的了。如今又左不盗,右不盗,偏偏把这碧玉搬指盗了去,这显然是存有一种深意,更是不容易对付啊。”只是各人对于对方所已懂得,而他自己倒尚未完全明了的部分,虽因小柬上的指点,也已有点瞧料出来,终究是有一些隔膜,一半儿明白,一半儿不明白,倒又使得他们都沉思起来了。最后,还是那少年先打破了这沉寂的空气,笑着说道:“这也是很平常的一种玩意儿,没有什么道理的。让我日后找着了他,和他好好的算帐就是了。如今让我先去通知黎一姑一声,立刻就来请你进去和她会面。”说完,径自向外走去。
不一刻,来了两个喽罗,说是奉了寨主的命,前来迎迓贵客的。柳迟便跟着他们走去,刚走至大寨之前,早见那个老者之外,还有一个叮扮得十分齐整的姑娘,在迎候着他,这当然就是那位巾帼英雄黎一姑了。可是,当柳迟刚向他瞧得一眼时,不觉怔呆了起来。原来,这黎一姑的面貌,竟有十分之九是和那个少年相肖的呢。比及到得寨中,相将坐下,柳迟方又想到小柬上所提起的那美人二字,不禁恍然大悟,这黎一姑和那少年,定是一而二,二而一着的呢。这时候,黎一姑似也知自己的行藏已被柳迟瞧破,便一笑,说道,“这只是一种游戏的举动,阁下想已完全明了,我们也不必再说的了。”于是,柳迟也只能一笑相报,并说明了不要假冒人家,而竟成了一个假冒者的那种原因。接着,大家淡得十分投机,方知那老者唤黎三丰,是黎一姑的一个族叔,正管理着寨中一切的琐事。而由黎三丰的口中,又知道黎一姑的祖父唤黎平,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同志,奉命随着某王来经营山东。后来,他的一部份人马,就长驻在登州、莱州一带的地方。等到太平天国覆灭,山东也为满清所收复,他就被清军捉了去。这时太平天国的旧部,投顺清军者虽是数不胜数,他却大义皎然,不为所屈,因此,便在省垣遇害了。当临刑的那一天,他偷榆的把一个碧玉搬指交给了狱卒,教他务要设法交到他独生的儿子黎明手中,作为一种纪念品。并说:
他一死尚在其次,太平天国如此的覆亡,实是十分痛心,他死也不得瞑目的,务望他的儿子不但须为他向满清复仇,还得时时以恢复太平天国为念。这狱卒,从前也是太平军中的人物,总算有点儿义气的,居然辗转访寻,不负所托,终竟把这碧玉搬指交到了黎明的手中。不料,黎明未将大仇报成,已是死了。只遗下了一个幼女黎一姑,便将祖父一番的遗命,转告诉了黎一姑,教他继续报仇。并说:“孤零零的一个女孩儿家,恐怕干不成什么大事,最好选择一个英雄人物而嫁之,那碧玉搬指,正不妨作为订婚时一种礼物呢。”因又把那碧玉搬指交给了他。而黎一姑从小就从名师习艺,有上了一身绝高明的本领,闻得了这一番遗命,和睹及这一件祖父的遗物,不兔恸哭一场。从此就在这青牛寨中,继续着他父亲的事业。原来,黎明为要有上一个根基地起见,早在这里落草的了。到了近日,招兵买马,悉心操练,更是很有上一番新的气象呢。
柳迟听了这番说话以后,方知这碧玉搬指非寻常的珍宝所可比,万万遗失不得的,不觉脱口而出的说道:“如此说来,我把这碧玉搬指丢失了去,更是罪该万死了。但既是这般珍贵的一件东西,黎寨主为什么随随便便的,交给在……”意思是要说:为什么要交给在一个不相识的人的手中,而且也不郑重的交代上一句?黎三丰不等他把这句
话说完,即搀言道:“柳兄是一个很通达的人,难道连寨主的这一点儿意思,也参透不来么?”这句话不打紧,却把这个巾帼英雄的黎一姑,也闹得一个粉脸通红,连连把眼睛瞪着他,似乎教他不要再说下去。便连柳迟也自悔一时失言,未免有些唐突美人,深探自疚之馀,倒也弄得有些局促不安了。但是这十分饶舌的黎三丰,也不知是否依仗着自已是黎一姑的叔父,有意倚老卖老,还是立时要想把他们撮合拢来,故意这么子的说。他竟象毫不理会似的,又接着说下去道:“而且我刚才不是曾对你说过,先兄故世的时候,曾嘱他须择一英雄夫婿而嫁之,不过,一向来到这里来拜山的,都是一些庸庸碌碌之人,那里有上一个什么英雄。现在,可绐我们遇到了。”他把这话一说,意思更是十分的明白:他已把柳迟目为一个英雄,并急急的要替他玉成了这头亲事呢。
现在,且把柳迟这一边暂行搁下。再说白马山所要请去的那个能人,究竟是什么人呢?原来,那人姓陈,名达,是杨赞化最小的一个徒弟,很具上有一种超群出众的本顿。因为白马山延请他去,具上有一种秘密的性质,生怕绐其他山寨中的人所知道,所以,他并不和白马山差去的使者一起同行,迟了几天方动身。不料,恰恰已是后了一步,人家竟把柳迟误认作了他,凡是受过白马山嘱托的几个客店,对于柳迟,招待得十分殷勤,供张得也十分丰富,对他却不怎样的理睬。
他最初见了,不免有些生气,想要把这一层误会立时揭他一个穿,继而一想:我们所以要如是做法者,不是为求秘密起见么?如今,既有一个冒名者充作我的前站。那是再好没有。就是这种秘密,已给我们的敌人们所探知,沿途倘然要出什么花样,也必指鹿为马的,把这冒名者当作我。
那一切都由这冒名者承当了去,可以与我无干,我不是反可脱去敌人们的监视,安然到达白马山了么。
他这么一想时,颇自以为得计。因此,也不去戳穿柳迟冒名顶替的这一层关系,只远远的跟随在后面,暗窥他的一切行动。等得到了住宿的那旅店中,店中人因为已把那贵客接得,对于这衣服并不十分光鲜,相貌并不怎样出众的一个客人,当然不会如何的注意。他也不把自己说破,和寻常旅客一般的,在一间小房中住下来了。然而柳迟入店后的种种举动,他都随时在那里窥着的。所以,那一晚在宴饮的时节,那乌大汉在院子中叫喊,以及镖未出手,自己先行栽倒的等等情节,都一一瞧在眼中,并连这乌大汉是如何的一种来意,他都有些猜料到的。不过,在那大汉中了暗器遁去以后,忽又从尾上跳跃下一个少年来,倒又使他暗中吃上一惊,但他所惊的,并不是在这少年的来得兀突,而在这少年的面貌,为何生长得如此的俊美。经他细细的一注意,方瞧出是女子乔装了的。后来,再一偷听到那美少年所说的一番言语,并暗窥到那美少年种种的举动,不禁恍然大悟道:“这不就是黎一姑所化装的么?我险些儿也给他蒙过了。”这一来,倒又把柳迟痛恨了起来,倘不是柳迟在前面冒充着他,这一番艳福,不是该归他所享受的么?比见黎一姑邀柳迟前去拜山,并以一个搬指交给柳迟作信物,显然有委身于柳迟的一种意思,更使他怒火中烧,气恼得什么似的,几经他在心中盘算着,方决定了,当柳迟前去拜山的时候,自己仍跟随了在一起走,并要当着黎一姑的面,想法把那搬指盗了来。自己能够这么的一显弄本领,那时候还怕美人几不十分的倾心于他么?
他把这个主意想定,觉得很是快乐,便安然的睡了去。到了第二天,柳迟抄着小路,前往青牛山拜山,他当然追蹑在后,只因十分留心,所以没有给柳迟觉察到。只有一桩:柳迟的前往拜山很是光明正大,所以乘了那老者的一艘小船前往。他却带上鬼祟的性质,生怕给人瞧见,不敢公然唤渡,直待至黄昏人静之际,方游过这条湖去,又偷偷的掩入了水寨中。幸仗他的水陆二路工夫,都是十分了得,居然过了一关又一关,早巳平安无事的,来到大寨之前。又给他捉着了两个巡更的小喽罗,在小喽罗口中,知道了这假冒者正住在那宾馆之中。他便把这两个巡更者捆缚起来,并絮住了他们的口,掷在树荫之下,方一个人前去行事。等到已是得了手,故意又把柳迟的被掣上一掣,让他惊醒过来,然后自己方走,这又是一种显弄本领的意思呢。不料,这时黎一姑也恰恰打外面回来,倘然真的向他追了去,虽不见得便能把他擒捉住,然当场必有上一番厮杀。
谁知黎一姑竟当他是一个小毛贼,不屑和他交得手,轻轻的放他走了去。于是,他一出得险地,也就向着白马山而来了。
白马山的李大牛,以前曾和他见过面的,见了他的到来,当然十分欢喜。一壁又带着惊讶的神情,向他问道:“你是打那条路走的?据我所派出去的一般小喽罗回来报告,说你昨日打从那家客店出来以后,好似失了踪的一般,我们正在惊疑不定呢。”他听了,不觉哈哈大笑道:“他们这一般人始终没有注意到我,怎知道我失踪?他们所报告给你听的,大概是别一个人的行踪,恐怕是与我无关的罢。”这一说,倒说得李大牛怔住了半晌,方又问道:“这是什么话?我教他们沿途留心着的,只有你一个人,怎么又会误缠到别一个人的身上去?”他又大笑道:“哈哈,老大哥,你真好似睡在梦中一般了,你不知道,象我这么一个无名小卒,还有人沿途冒着我的名儿呢。你想他们都是不认识我的,怎又弄得清楚这一件双包案呢?”李大牛不免更是惊诧道:
“怎么还有冒名的人?我真一点儿也不知道。”当下,他便把沿途一切的情形,约略说上一说。
李大牛方始恍然大悟。他便又把这碧玉搬指取了出来,说道:“这冒名的人,已往青牛山寨中去了,我也跟着他同去了一遭。这就是我在那里得来的一件胜利品呢。”
李大牛一听,凝目把这碧玉搬指望上一望,现着惊诧的神气,向陈达问道:“这不是从黎一姑那里得来的么?我听说黎一姑随身佩带着这么一件东西,是他父亲的遗物,留给他作为纪念品的,遇着可意的人儿便不妨拿来作为私订终身的一种表记。难道黎一姑已看中了你这一表人才,把这宝物赠给你作为表记么?”陈达又笑着点点头道:“你这话虽不中,也不远矣了。大概这件宝物既能归我所有,这个美人儿也不久就能为我所拥有罢。”他这话一说,不免引得李大牛深深的向他瞧视一眼,暗地似乎耽上了一种心事。他这种心事,倒也不难猜度而得的。原来他所最最畏惧的,就是这青牛山寨的黎一姑,所以要千方百计的,把这陈达请了来,作上自己的一个帮手,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如今这陈达倘然竟搭上了黎一姑,那他不助自己,而反助黎一姑,乃是显而易见的事,不是反有揖盗入室之嫌么?一壁却又装着满脸笑容,赶紧的说道:“这倒是很可贺的一桩事,我想邀集了全寨的头目,好好的为你称庆一番呢。”
等到筵席摆上,正在欢饮之际,忽有小喽罗来报:有一个姓柳的前来拜山,并指名要见新到山寨的陈寨主。陈达就知定是柳迟来了,不禁笑道:“这厮原来姓柳,他倒已是把我打听得一个清楚,夹屁股就赶了来了。好,就请他进寨来罢。”一壁便也起身相迎。两下见面之下,谁知竟是非常的客气,一个赶着行礼,一个也赶着还礼。比及行礼已毕,大家仰起身来,方在陈达的身上,发见了柳迟的足印,而柳迟的袜上,也发见了陈达指头的影痕。不觉默喻于心,相视一笑。
李大牛虽立在陈达的身旁,却一点儿也没有知道,只顾把柳迟当作一位贵客,尽向着里边让。一到厅上,他便又笑吟吟的说道:“不知柳兄远来,未曾备得酒席。不嫌这是残肴,就请坐上来饮啖一会,等晚上再专诚奉清罢。”
柳迟倒并不客气,只把头微微一点,即在李大牛所向他指点的那个席位上坐下。但是屁股刚一坐下,只闻得格列的一声响,一具很坚厚的楠木的椅子,竟给他坐坍了。这在柳迟,明明是有上一种卖弄本领的意思,小小的用上一点功劲,就把这楠木椅子弄坍了。可怜这李大牛,却还是蒙在鼓里,一点儿也不明白,反连声的责骂着小喽罗,说他们办事怎么竟如此的不留神,把破坏不坚的椅子,拿出来给客人们坐,倘然把客人跌上一大跤,这还了得么。陈达却只是在旁边冷笑着。这时候,挨骂的小喽罗们,早又另换了一把椅子来,虽也是楠木的,却比先前的那一把,更坚厚得多了。但是奇怪,柳迟的屁股,刚和这椅子作上一个接触,复闻得格列的一声响,这椅子又是坍坏了。这一来,李大牛也明白过来,知道这是来客故意这般的做作,要在他们面前卖弄上一点本领的,倒又愣着在一旁,弄得没有什么方法可想。但陈达在这时候,再也不能在旁边冷眼瞧着了,只向厅外的庭中瞧得一眼,早已得了一个主意。即见他不慌不忙的向庭中走了去,跟着就把一个很大的石鼓儿,一手托了进来。这石鼓儿看去怕不有二三百斤重,他托在手中,却面也不红,气也不喘,好象没有这回事一般。进得厅来,很随意的一脚,即把地把已坍坏了的楠木椅子,踢至数丈之远,为墙壁所挡靠住了。但墙壁受不住这般大的一股激力,早有些个粉垩,纷纷从上面落下。陈达却就在这当儿,将身微偻,用手轻轻的一放,这石鼓儿,便端端正正的放在席面前了。一壁含着微笑,向柳迟说道:“刚才的那两把椅子,委实太不坚牢了,竟经不起阁下这重若泰山的身躯一坐。如今没有方法可想,只好端了这石鼓儿,委屈阁下坐一下,倘然再要坍坏的话,那兄弟也就没法可想了。”这明明是含有讥诮的意味,以报复他的故意使刁。柳迟那有不理会之理,也只有谦谢的分儿,心中却在那里暗想:“这小子倒真可以,我不过要在他们的面前献上一点本领,作上一个示威的运动,不料他献出来的本领,倒比我更高一步了。这我此后倒要步步小心,倘变成了鸿门宴上的沛公,弄成来得去不得,那才是大笑话呢。”
于是,大家又相将入席。酒过三巡之后,忽有一件东西,从梁上掉落下来,恰恰坠落在肴菜之中,细看,却是一根小小的稻草儿。李大牛见了,不觉笑道:“好顽皮的燕子儿,竟把这样的东西,来奉敬嘉宾了,未免太寒蠢一点罢。”细听,果有燕子呢喃的声音发自梁上,怕不是他们闹的顽意儿。这时候,柳迟倒又忘记了自己警告自己小心一点儿的那句说话,痒痒然的,又想在他们的面前,献弄上自己的一点绝技了。原来他的身子,近年已练得同猴子一般的轻捷,蹿高落下,不算得什么一回事的。只见他仰起头来,向着梁上一望,含笑说道:“果然是头顽皮的燕子,在向着我们开玩笑。但我自问顽皮的本领,倒也不下于人,颇想捉着了它们问上一声,究竟谁是比谁会顽一些呢?”不知柳迟捉得了这头燕于役有?且待第—百五十八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