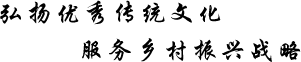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梦古镜还魂 仲禹抡元熊飞祭祖
且说包公听见包兴说在阴司地府,便厉声道:“你这狗才,竟敢胡说!”包兴道:“小人如何敢胡说。只因小人去过,才知道的。”包公问道:“你几时去过?”包兴便将白家堡为游仙枕害了他表弟李克明,后来将此枕当堂呈缴。因相爷在三星镇歇马,小人就偷试此枕,到了阴阳宝殿,说小人冒充星主之名,被神赶了回来的话,说了一遍。包公听了“星主”二字,便想起:“当初审乌盆,后来又在玉宸宫审鬼冤魂,皆称我为星主。如此看来,竟有些意思。”便问:“此枕现在何处?”
包兴道:“小人收藏。”连忙退出。不多时,将仙枕捧来。包公见封固甚严,便叫:“打开我看。”包兴打开,双手捧至面前。包公细看了一回,仿佛一块朽木,上面有蝌蚪文字,却也不甚分明。包公看了,也不说用,也不说不用,只是点了点头。
包兴早已心领神会,捧了仙枕来到里面屋内,将帐钩挂起,把仙枕安放周正。回身出来,又递了一杯茶。包公坐了多时,便立起身来。包兴连忙执灯引至屋内。包公见帐钩挂起,游仙枕已安放周正,暗暗合了心意,便上床和衣而卧。包兴放下帐子,将灯移出,寂寂无声,在外伺候。包公虽然安歇,无奈心中有事,再也睡不着,不由翻身向里。头刚着枕,只觉自己在丹墀之上,见下面有二青衣牵着一匹黑马,鞍辔俱是黑的。忽听青衣说道:“请星主上马。”包公便上了马。一抖丝缰,谁知此马迅速如飞,耳内只听风响。
又见所过之地,俱是昏昏惨惨,虽然黑暗,瞧得却又真切。只见前面有座城池,双门紧闭。那马竟奔城门而来。包公心内着急,说是不好,必要碰上。一转瞬间,城门已过,进了个极大的衙门。到了丹墀,那马便不动了。只见有两个红黑判官迎出来,说道:“星主升堂。”包公便下了马,步上丹墀。见大堂上有匾,大书“阴阳宝殿”四字。又见公位桌椅等项俱是黑的。
包公不暇细看,便入公座。只听红判道:“星主必是为阴错阳差之事而来。”便递过一本册子。包公打开看时,上面却无一字。才待要问,只见黑判官将册子拿起,翻上数篇,便放在公案之上。包公仔细看时,只见上面写着恭恭正正八句粗话,起首云:“原是丑与寅,用了卯与辰。上司多误事,因此错还魂。若要明此事,井中古镜存。临时滴血照,嗑破中指痕。”当下,包公看了,并无别的字迹。刚然要问,两判拿了册子而去。那黑马也没有了。
包公一急,忽然惊醒,叫人。包兴连忙移灯近前。包公问道:“什么时候了?”包兴回道:“方交三鼓。”包公道:“取杯茶来。”忽见李才进来禀道:“公孙主簿求见。”包公便下了床,包兴打帘,来至外面。只见公孙策参见道:“范生之病,晚生已将他医好。”包公听了大悦,道:“先生用何方医治好的?”公孙回道:“用五木汤。”包公道:“何为五木汤?”公孙道:“用桑、榆、桃、槐、柳五木熬汤,放在浴盆之内,将他搭在盆上,趁热烫洗,然后用被盖严,上露着面目,通身见汗为度。他的积痰瘀血化开,心内便觉明白。现在惟有软弱而已。”包公听了,赞道:“先生真妙手奇方也!即烦先生好好将他调理便了。”公孙领命退出。包兴递上茶来。包公便叫他进内取那面古镜,又叫李才传外班在二堂伺候。
包兴将镜取来。包公升了二堂,立刻将屈申并白氏带至二堂。此时,包兴巳将照胆镜悬挂起来。包公叫他二人分男左女右,将中指喳破,把血滴在镜上,叫他们自己来照。屈申听了,咬破右手中指,以为不是自己指头,也不心疼,将血滴在镜上。
白氏到了此时,也无可如何,只得将左手中指咬破些须,把血也滴在镜上。只见血到镜面,滴溜溜乱转,将云翳俱各赶开,霎时光芒四射,照得二堂之上,人人二目难睁,各各心胆俱冷。
包公吩咐男女二人,对镜细看。二人及至看时,一个是上吊,一个是被勒,正是那气堵咽喉,万箭攒心之时,那一番的难受,不觉气闷神昏,登时一齐跌倒。但见宝镜光芒渐收。众人打了个冷战,却仍是古镜一面。包公吩咐将古镜、游仙枕并古今盆,俱各交包兴好好收藏。再看他二人时,屈申动手动脚的,猛然把眼一睁,说道:“好李保吓!你把乐子勒死倒是小事,偷我四百两银子倒是大事。我和你要定咧!”说着话,他便自己上下瞧了瞧。想了多时,忽把自己下巴一摸,欢喜道:“唔,是咧!是咧!这可是我咧。”便向上叩头:“求大人与我判判。银子是四百两呢,不是顽的咧。”此时,白氏已然苏醒过来,便觉羞容凄惨。包公吩咐:“将屈申交与外班房,将白氏交内茶房婆子好生看待。”包公退堂歇息。
至次日清晨起来,先叫包兴问问公孙先生,范生可以行动么?去不多时,公孙便带领范生慢慢而来。到了书房,向前参见,叩谢大人再造之恩。包公连忙拦阻道:“不可,不可。”看他形容虽然憔悴,却不是先前疯癫之状。包公大喜,吩咐看座。
公孙策与范生俱告了坐。略述大概,又告诉他妻子无恙,只管放心调养。叫他无事时将场内文字抄录出来,”待本阁具本题奏,保你不失状元就是了。”范生听了,更加欢喜,深深的谢了。包公又嘱咐公孙好好将他调理。二人辞了包公,出外面去了。
只见王朝、马汉进来禀道:“葛登云今已拿到。”包公立刻升堂讯问。葛登云仗着势力人情,自己又是侯爷,就是满招了,谅包公也无可如何。他便气昂昂的一一招认,毫无推辞。
包公叫他画了招。相爷登时把黑脸沉下来,好不怕人,说一声:“请御刑!”王、马、张、赵早巳请示明白了,请到御刑,抖去龙袱,却是虎头铡。此铡乃初次用,想不到拿葛登云开了张了。此时,葛贼已经面如土色,后悔不来,竟死于铡下。又换狗头铡,将李保铡了。葛寿定了斩监侯。李保之妻李氏,定了绞监候。业道士盗尸,发往陕西延安府充军。屈申、屈良当堂将银领去。因屈申贪便宜换驴,即将他的花驴入官。黑驴伸冤有功,奉官喂养。范生同白氏玉莲当堂叩谢了包公,同白雄一齐到八宝村居住,养息身体,再行听旨。至于范生与儿子相会,白氏与母亲见面,自有一番悲痛欢喜,不必细表。
且说包公完结此案,次日即具折奏明:威烈侯葛登云作恶多端,已请御刑处死;并声明新科状元范仲禹,因场后探亲,遭此冤枉,现今病未痊愈,恳恩展限十日,着一体金殿传胪,恩赐琼林筵宴。仁宗天子看了折子,甚是欢喜,深嘉包公秉正除奸,俱各批了依议。又有个夹片,乃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因回籍祭祖,告假两个月。圣上亦准了他的假。凡是包公所奏的,圣上无有不依从。真是君正臣良,太平景象。
且说南侠展爷既已告下假来,他便要起身。公孙策等给他饯行,又留住几日,才束装出了城门。到了幽僻之处,依然改作武生打扮,直奔常州府武进县遇杰村而来。到了门前,刚然击户,听得老仆在内说道:“我这门从无人敲打的。我又不欠人家帐目,我又不与人通来往,是谁这等敲门呢?”乃至将门开放,见了展爷,他又道:“原来大官人回来了。一去就不想回来,也不管家中事体如何,只管叫老奴经理。将来老奴要来不及了,那可怎么样呢?哎哟,又添了浇裹了。又是跟人,又是两匹马,要买去也得一百五六十两银子。连人带牲口,这一天也耗费好些呢。”唠唠叨叨,聒絮不休。南侠也不理他,一来念他是世仆老奴,二来爱他忠义持家,三来他说的句句皆是好话,又难以驳他。只得拿话岔他,说道:“房门可曾开着么?”
老仆道:“自官人去后,又无人来,开着门预备谁呢?老奴怕丢了东西,莫若把门锁上,老奴也好放心。如今官人回来了,说不得书房又要开了。”又向伴当道:“你年轻,腿脚灵便,随我进去取出钥匙,省得我奔奔波波的。”说着话,往里面去了。
伴当随进,取出钥匙,开了书房。只见灰尘满案,积土多厚。
伴当连忙打扫,安放行囊。展爷刚然坐下,又见展忠端了一碗热茶来。展爷吩咐伴当接过来,口内说道:“你也歇歇去罢。”
原是怕他说话的意思。谁知展忠说道:“老奴不乏。”又说道:“官人也该务些正事了。每日在外闲游,又无日期归来,耽误了多少事体。前月,开封府包大人那里打发人来请官人,又是礼物,又是聘金。老奴答言,官人不在家,不肯收礼。那人哪里肯依,他将礼物放下,他就走了。还有书子一封。”说罢,从怀中掏出,递过去道:“官人看看,做何主意?俗语说得好:‘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也该奋志往上巴结才是。”南侠也不答言,接过书来,拆开看了一遍,道:“你如今放心罢,我已然在开封府作了四品的武职官了。”展忠道:“官人又来说谎了。做官如何还是这等服色呢?”展爷闻听,道:“你不信,看我包袱内的衣服就知道了。我告诉你说,只因我得了官,如今特特的告假回家祭祖。明日预备祭礼,到坟前一拜。”此时伴当巳将包袱打开。展忠看了,果有四品武职服色,不觉欢喜非常,笑嘻嘻道:“大官人真个作了官了,待老奴与官人叩喜头。”展爷连忙搀住道:“你乃是有年纪之人,不要多礼。”
展忠道:“官人既然作了官,总以接续香烟为重,从此要早毕婚姻,成立家业要紧。”南侠趁口道:“我也是如此想。前在杭州有个朋友,曾提过门亲事。过了明日,后日我还要往杭州前去联姻呢。”展忠听了道:“如此甚好。老奴且备办祭礼去。”
他就欢天喜地去了。
到了次日,便有多少乡亲邻里前来贺喜,帮忙往坟上搬运祭礼。及至展爷换了四品服色,骑了高头大马到坟前,便见男女老少俱是看热闹的乡党。展爷连忙下马步行,伴当接鞭牵马,在后随行。这些人看见展爷衣冠鲜明,相貌雄壮,而且知礼,谁不羡慕,谁不欢喜。你道如何有许多人呢?只因昨日展忠办祭礼去,乐得他在路途上逢人便说,遇人便讲,说:“我们官人作了皇家四品带刀的御前护卫了,如今告假回家祭祖。”因此一传十,十传百,所以聚集多人。且说展爷到了坟上,礼拜已毕,又细细周围看视了一番。见坟冢树木俱各收拾齐整,益信老仆的忠义持家。留恋多时,方转身乘马回去。便吩咐伴当,帮着展忠张罗这些帮忙乡亲。
展爷回家后,又出来与众人道乏。一个个张口结舌,竟有想不出说什么话来的。也有见过世面的,展老爷长,展老爷短,尊敬个不了。展爷在家一天,倒觉得分心劳神。定于次日起身上杭州,叫伴当收拾行李。到第二十日,将马扣备停当,又嘱托了义仆一番,出门上马,竟奔杭州而来。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