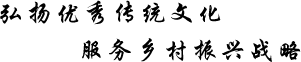八十八回 引经典皇心难改变 说前事兄弟再联手
雍正惊得呆住了,他想不到引娣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哦,你有这样的心吗……你如果死了,朕定要下令处死允禵,绝不宽容!”说完这话,他忽然觉得一阵头晕,便惶惑地向乔引娣看了一眼,又转身走了……
雍正皇帝冲风冒雪在半夜里来到允祥这里,是因为前晌在乔引娣那里受了冷遇,又不能发火,他睡不着,也坐不住,这才拉着张廷玉出来的。听见允祥在问他,他像是被恶梦惊醒了似的说:“啊?你刚才说的什么……哦,对了,你说的是兄弟之事……朕何尝不想兄弟同心?要知道,他们确实不是‘等闲之辈’呀!你们看看这几年里,想作乱的有多少?隆科多、年羹尧倒也罢了,如今老八又提出‘整顿旗务’了。好啊,既然他们这样地锲而不舍,朕也只好奉陪到底了。”他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包药来,李卫连忙给他倒好了水送来,看着他把药吃掉。却见他苦笑着摇摇头说:“唉,这药可真苦啊!可是,不吃又不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嘛。廷玉,李卫,你们有什么也索性全说出来吧,不管你们说了什么,朕都许诺言者无罪。”
张廷玉神色庄重地说:“皇上既然这样诚恳地求谏,老臣就放肆直言说说心里话。老臣知道,当皇帝难,难得很哪!李世民曾经说过:‘人主只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馅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而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从皇上还当着皇子的时候,您不就是总在受着攻击吗?但臣以为,只要皇权不旁落,人臣们的‘勇力’就难动其心;而人主聪察明断,那些所谓的‘辩口’,‘谄谀’、‘奸诈’也难施其伎。唯有这‘嗜欲’二字,是天性中自带的,如果不在‘克己’上下真功夫,就难免要堕入小人们的迎合之中。”
雍正含笑地问:“廷玉,那你就说说朕有什么‘嗜欲’。你不妨明说,朕绝不会怪你的。’、
允祥和李卫听到这里,都觉得张廷玉一定要说乔引娣的事。不料张廷玉却说:“主上的‘嗜欲’就在于‘急于事功’。下面的臣子看准了这一条,也就会千方百计地投主所好。藩库亏空,是几十年积下的,主上下令要在三年内还清,这就是急于事功之一例。先是湖广虚报亏空补完,李绂一本奏上,几个方面大员被罢了职务;山西诺敏假冒邀功,又死于非命。他们当然是罪有应得,可是,朝廷逼得太严,也不能不说是其中的原因。还有,皇上曾说过,‘不言祥瑞’,也确实对下边说的好听话不予理睬。可是,皇上的心里却是在盼着祥瑞的。鄂尔泰上书说,古州一个月之内,七次见到‘卿云’,皇上表示了惊奇和赞叹。十三爷这里的刘统勋当时就在古州,臣问他:‘卿云’是什么样子,他却说哪有那事儿啊!还有人报称某地万蚕同织一茧,长五尺八,宽二尺三,这明明是在说假嘛,可皇上还是让宣布了!田文镜本是清廉的官员,最近也来凑热闹,他奏报说‘河南嘉禾瑞谷,一茎十五穗’。可是,河南不是还照样荒欠吗?老臣不是说不该报这些祥瑞,而是说,只要主上心里稍有嗜欲,就会使下边的人想方设法地来迎合。时间一长,哪是真的,哪是假的,谁也难以分辨了。”他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看了看雍正的脸色,便接着又说,“嗜欲有各个方面。老臣是从小就看着主上的,深知皇上不好酒,更不贪色。最近外面传言很盛,说的全都是乔引娣的事。臣不信,也不愿信!但臣还是要说,天子无私事!在国与家上面,皇帝与平民是绝不相同的。老臣这话,敬请皇上参酌。”
张廷玉说完,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李卫在旁边不禁暗自佩服:好,张廷玉从小事入手,渐渐地说到本题,确实比别人说皇上是“好色误国”要有用得多,这姜还是老的辣呀!他一边恩忖一边说道:“张相说的那些,真让奴才长了见识;奴才是在主子身边长大的,这些年在外头做官,也确实看到了官场的积弊。比如这‘揣摩’二字,奴才就对它没辙。你能献四个穗的谷子,我就能给你弄来个二十四个穗的。反正只要哄得主子高兴,就是不能升官,起码也不会被罢了官。我也说过假话,后来才与主子交了底的,主子也没有怪我。再比如,早年间,我曾经把八爷府上的照壁都卖了,八爷也没有生气,因为那是私事,是小事。可现在遇上了国事、大事,八爷可就不肯让步了。奴才识字不多,只是看到戏文里说:女人祸国。奴才就想,哪朝哪代不全是男人当家呢?男人们要是不愿意,女人能替你办事儿吗?她能拿着你的手写圣旨?就算乔引娣的事是真的吧,奴才看皇上也犯不着为了她和十四爷闹生分。不说别人,我看着这丫头就觉得别扭。我是审过诺敏一案的,天天都能见到这个毛丫头,塌肩膀,水蛇腰,大脚片子足有四寸长,有什么好看的?”李卫心里明白,反正他识字不多,皇上又说了言者无罪,于是,他就东一榔头,西一棒棰地胡说,但句句说的都是讽劝。一直说得连张廷玉都笑了,他才住了口。
他们这里说得热闹,可没想到雍正的心里是多么难受。雍正一想到早上的情景,就忍不住要掉眼泪。他不易觉察地蹙了一下眉头说:“你们都在与朕闹弯弯绕,朕怎么能听不出来?允禵咆哮先帝灵堂,不遵太后教令,他不守法,不敬上,是有罪的人。从公的方面说,朕应当换掉他身边侍候的人;从私的方面说,他是朕的兄弟,朕也不愿他过份地伤情。朕体谅你们的好心,就再放他一马。允祥可以写信告诉他,他愿意在那里守灵也好,愿意回到京城来作事也可,三年之内,只要他能自省改过,朕都把他看作好兄弟,万事都可商量。可他要硬往那个‘党’里钻,一味地和朕唱对台戏,朕也就对他无可救药了。”他说完就站起身来,李卫连忙上前,扒了许多烧红了的炭火,替雍正装好了手炉,又护送着他离开了清梵寺。
外面雪下得很大,地上的积雪也已有半尺来厚。可是,李卫和允祥等人却没有想到,就在今晚,就在雍正他们说话的时候,还有一些人也是在通宵达旦地计议着!这就是八爷允禩、九爷允禟和他们的几个亲信。
这里是八爷府的一座暖阁,它的一半压在水面上,另一面则建在水里。靠水的三面,全装着落地的双层大玻璃窗。冬天,坐在花厅里就可以欣赏到雪景,夏天则可临窗垂钓。为了保暖,这厅里的柱子全都是空心的铜板,地下通着熏笼,熏笼通着铜柱。允禩是很会享受的,他又爱暖和又爱赏雪,为了不让这花厅显出雪化了的情景,他又特意让工匠们在花厅顶上苫了半尺厚的黄笔草。所以,哪怕再冷的天,花厅里却仍然是温暖如春。据说,光这座花厅,就化了四万两银子。这样的屋子,不但别的王府没有,就连皇宫御苑,也难得一见。
此刻,这里的人们都早已是酒足饭饱,但等着听八爷的训话了。允禩清了清嗓子说:“诸位,今天我再说什么全都是多余的,我们已到了图究匕首现的时候了!我们这些‘鱼肉’,眼见得已被送上砧板成为刀俎,就是不想跳也不行了。”他说话的语气还和平日一样,话虽尖刻,但却说得极其平和,丝毫也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口气。“八贤王”的名气,朝廷上下,人人皆知,他的沉稳平和,在朝中也一向是为人敬佩的。
允禟就坐在他的旁边。他比允禩只小两岁,可看上去却要老得多。不但又黑又瘦,说出话来也特别的老辣:“八哥说得一点不假,老四既然一心让我们过不去,那就和他老账新账一齐算吧。内廷有人送信给我说,一开春允祥就要把我送到岳钟麒的大营去。所以,这事一定要赶到正月十五之前。刚过完新正,人心正散。葛达浑管着礼部,又是文华殿的大学士,你就趁着那时候,把来京的王爷们请去。题目一摆出来,他雍正不想见也得见。”他站起身来,在花厅上踱着步子说:“我们错过了多少机会呀!圣祖殡天时,我们之中如果有一人在外面,还能让允祥到丰台去杀人夺兵权?允祥后来去哭灵时,我们要趁机大闹一场,隆科多敢宣布那份假遗诏?允禵要是不奉诏进京,而是驻在西宁按兵不动,或者带兵视事,八哥再在朝堂上一呼,他雍正能坐得稳皇位?隆科多那次搜宫,如果再早上一天,雍正还不就得当流亡皇帝?我在西宁军中时,如果狠一下心,亲手杀了刘墨林那个浪荡钦差,年羹尧也可能早就在西宁自立为王了。我这样说,不是在指责谁,而是说我们把大好的机会全都错过去了,按理说,上天早就该厌弃我们了。可是,他还在给我们机会,还在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地干下去。我们难道能再一次失之交臂吗?”
“老九,你别再说下去了。”允禩的脸色通红,心中好像充满了悔恨,“以前种种,全怪你的八哥心太软,总想平平稳稳地干,不要弄乱了朝局。再说,我们手里也缺着一个能翻天覆地的孙大圣,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勇猛之上呀!我仔细地想过了,这次只要闹起来,就不要轻易罢手,看他雍正怎么来收拾这个混乱的局面。”
葛达浑眼睛熬得通红,他抚摸着脑门子说:“我管着文华殿,那里的太监们也都肯听我的。皇上无道,他擅改先帝的遗法,欺母逼弟,暴虐群臣,早就激起大家的不满了。可我担心的有三条:一,我们没有兵权;二,如今君名份已定,我们这样做是不是造逆?万一有的督抚要起兵勤王,我们拿什么去抵挡?三嘛,人旗旗主现在只找到了四位。这些人平日里什么事都不管,只敢在背后发发牢骚,一旦到了和皇上对阵之时,他们会不会下软蛋?这些假如不事先想好,预备得不充分,失利事小,正如九爷所说,我们可是赢起输不起了啊!”
允禟却笑着说:“老葛,你太多虑了,我们只是把这些旗主们拿过来用一用,并不是叫他们上阵的。这棋,要分作几步走呢!整顿旗务是老四亲自下的旨意,我们按照他的意思叫旗主们来京,有什么罪过?雍正整顿旗务的宗旨是两条:一条是让旗人自谋生路,接着就削减旗人的月例钱;二是怪下五旗披甲人统属不明,不务正业。我们就先从第二条做起,在京各旗营的牛录管带的名单我早备齐了。旗主一来,先通知他们去晋见各自的旗主。旗主不是能对下属施行赏罚之权吗,只要他们见了旗主,谁再说什么都没用了。这样,下五旗的兵权我们就拿到手了一半!就说毕力塔这小子吧,他是汉人,可他下边的三个佐领都是旗人。旗人一见了旗主,毕力塔再说话还能有分量吗?然后,我们再推动第一条,让旗人们反对分田自种,因为这是坏了圣祖的成法。你们别看这些王爷平日里任事不管,可他们一旦到京,又听了奴才们的撺掇,不跟着造反,那才是怪事呢?如今朝廷上布满了干柴,到时候,八哥出来一声招呼,看谁能收拾了这个局面?”
老八听到这里连忙接口说:“不不不,收拾局面的应该是八旗旗主,他们要共管朝政。我们不是乱臣贼子,我们也没有篡位的心,更治理不了这个天下。应该说,天下的事情要天下公管!下五旗的王爷能来四位,我自己是正红旗的旗主,下五旗可以算是全都齐了。上三旗归雍正统属,镶黄旗是弘历,正黄旗是弘时,镶红旗是弘昼。你们一定要记住,弘时才是我们要拥戴的新主子呢?他想的是夺位,我们要的是实权。这样号召起来容易,也没有后顾之忧。诸位,都听明白了吗?”
阿尔松阿说:“这好办,我还是镶红旗的第二佐领呢,明天我就去见弘昼。别看他平时不管事,可谁也不敢得罪他。前年隆科多派人搜宫时,他正在家里忙着烧丹炼汞。弘时没和他打招呼,他火了,说东华门这里是他的丹炉罡斗正位,硬是不让兵士们进去。这位五爷后来还专门去向弘时‘请教’,问为什么要打搅他的静修?弄得弘时只好向他赔罪才算了事。”
允禩笑了:“那好啊,你就去和他好好聊聊,用不着扯正题,我们不要误了他的成仙之道。我这里正好有一本元版的《金丹正义》,你带去恭送给你家五爷吧。”
阿尔松阿刚随口提到了隆科多,倒让允禩心里好一阵惋惜:此人虽然被抄了家,可是京师旧部多得很哪,要是能把他也收拢过来,这是一支多么大的势力呀!就在这时,一个家人走了进来,在允禩的耳边悄悄他说了句什么。允禩高兴得大笑一声:“好,想曹操,曹操就来,这就是我们的福份,快请他到书房见面。苏奴,你是我的侄儿,和我一同去见他更好。”
允禩他们来到书房时,一眼就瞧见站在那里徬惶无措的隆科多。允禩叫了一声:“舅舅安好?”苏奴也连忙打下千儿去说:“给老舅爷请安!”
隆科多转过身来说:“不,这里只有隆科多,哪来的什么舅舅、舅爷的?不瞒八爷,我今天可是夜猫子进宅呀!”
允禩一笑说道:“舅舅不说我也知道,您一定是在怪我。上次皇上派兵抄您的家时,您叫人送来十万银票让我代为保存,我却又给您退了回去。这不是我不想管您的事,而是您不该送到我这里来。您想啊,在朝野的官员们都抄了上千家了,我这里还哪有安全可言?他雍正生就的是个抄家皇帝嘛!”允禩说着话,从书架里的一本书里拿出了一片小纸递给隆科多:“舅舅,这是我在顺义置办的一处庄子,十三万本银。按例,抄家是只抄浮财而不抄祖产的。所以,我把日期往前边提了十年,您留着它预防万一吧。谁能知道,明天又会是个什么局面呢?”
隆科多接过来稍微一看,就收进了怀里:“八爷,这事虽不大,可它足见你的心田,我就大恩不言谢了。说实话,我今夜冒死前来,挂念的就是那份玉碟呀。现在我的家虽被抄了,可家私还都没动。我的情形八爷心里比我更清楚,只要皇上说句话,要杀要砍还不是现成的?那时,我要这房产又有何用?可是,那份玉碟是弘时从我那里借去的,我刚刚去了三爷府,他却说是在你这里。老奴才请八爷赏脸,把它赏还给奴才吧。内务府一旦知道了,连累的人可就多得数不清了啊!”说着,他的两行老泪已经潸然而下。
其实允禩带着苏奴一块来,就想到了隆科多非要提起玉碟这件事的。不过,他可不想就这样地便宜了隆科多,倒想借苏奴之口,试一试隆科多的心事。
他知道,别看苏奴这小子不是近支皇亲,可却是皇亲贵戚中有名的“闷猴”。这小子从小就聪明伶俐,善于钻营,二十多岁时就被康熙看上了。老爷子当时说:想不到我们爱新觉罗家族里,还有这样一个天才。几年功夫,这个苏奴就当上巡抚了。今天他也在这里,拿他来做个枪手,是最合适不过了。苏奴当然也懂得八叔的心思,便笑着说:“老舅爷,您要的那份玉碟,小的背都背下来了,它值得您这样害怕吗?”
隆科多惊得大叫一声:“怎么你也看过了?天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