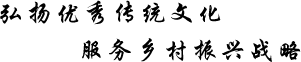三十 洪经略变节逢罡煞 小毛子遭难遇观音
康熙在慈宁宫给大皇太后和皇太后请过晚安,回到养心殿已是掌灯时分。苏麻喇姑歪坐在脚踏子上正埋头瞧着一张纸,竟没有觉察他已进来。
康熙笑着说:“婉娘,看什么呢,这样专心?”
苏麻喇姑这才抬起头来:“啊,皇上回来了,伍先生今儿个去风氏园抄了这几首诗回来,奴才正要恭呈御览呢。”
康熙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前明遗老怀念故园的伤情诗,不禁皱起了眉头“唔……伍先生是怎么看的。”
苏麻喇姑见康熙神色郑重,便说:“伍先生以为,这几首诗均系前明遗老之作。这些人骨气是有的,才气更不必说,只可惜不识大体,不随潮流,不顺民情,不明天理,也不懂得过是劫数造化所致,眼下还说不上如何劝化他们。”
廉熙听了;默然不语。这话正点在他的心病上:顺治爷是在马上得的天下,可朕却不能在马上治之。前明的这些宿儒名流不肯为我所用是件大事。对他们不能一概斩尽杀绝;但也不能由着他们散处林泉,去吟风弄月,指斥时政。那样,可惜了人才还在其次,搅乱了人心便不得了。想到这里,他突然转身问道:“伍先生可讲过对这些人有何善策?”
苏麻喇姑答道:“回主子,伍先生说,他自己并不赞同这些人。不过,人各有志,他们又没有几个人,万岁爷何必为此忧心呢?再说,现在也不是想这事的时候呀。”
康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这事要想得远一些。你应该知道,他们都是些人才,弃置山野朕心不忍。而且正道不行,就会生邪。”见苏麻喇姑正在凝神细听,康熙接着说:“曼姐儿,你听说过洪承畴江南罢宴的故事吗?”
于是,康熙便向苏麻喇姑讲了这个清初轰动一时的故事:
顺治七年的时候,多尔衷攻占江宁,南方半壁河山,尽归清朝,全国大局也已粗定。多尔衮回北京面君述职,留下洪承畴镇守金陵。这洪承畴呢,原是明朝崇祯皇帝的亲信大臣,担任蓟辽总督,统兵山海关外,抵抗清军。不料将骄兵情,战事失利。以致全军复没,洪老头也当了清军的俘虏。崇祯皇帝是个刚愎自用的人。朝政混乱,耳目不旺。他听信了传言,以为洪承畴必定会骂敌而死,便命人在京城为洪承畴建立新闻社祠堂,还亲自写了一篇《悼洪经略祭文》,要御驾亲临,祭奠这位明朝的大忠臣,以此鼓舞士气。不料就在开祭的那天早晨,传来洪承畴已经归顺清朝的消息。气得崇祯差点儿背过气去。
这洪承畴投降之后,确实为清军入关立下了大功。多尔衮把他留在金陵,就是想利用洪承畴在前明的威望,号召江南士子,归顺大清国。洪承畴因为自己深得顺治皇上和多尔衮的信任,也志得意满,在金陵城内,大宴三日,犒赏全军将士,祭奠南征亡灵。前两天,一切顺利,可是到了第三天的中午,正在吃西中间,突然门上通禀,说有一个姓吴的门生,要求见老师洪大人。把他引进来之后,他一不见礼,二不饮酒,却对洪承畴说:
“老师鞍马劳顿,学生也屡经战乱,学业都荒疏了,近来得到一篇绝妙文章,想与老师一同赏析。”
洪承畴一听,就不耐烦了。这儿正吃酒呢。看什么文章啊。便说:
“我老眼昏花,看不清文章了。”
“不妨,老师稳坐,待学生读给您听。”说完,从袖里掏出一卷文书,朗声开读。这一读不要紧,把洪承畴弄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满座的人,也无不变色。原来,这篇文章正是崇祯皇帝亲自写成的那个《悼洪承畴祭文》。洪承畴一气之下,把那个姓吴的杀了。
苏麻喇姑听完,也是大吃一惊:
“万岁,这个人怎么这么大胆!”
“不是大胆,朕看是有骨气。如果当时朕也在场,绝不能让洪承畴杀他。”
“为什么,他们忠于明朝,反抗大清,你也能赦兔吗?”苏麻喇姑不解地问。
康熙正色说道:“嗯。文人学士都重气节。他们读了书,抱着个忠臣不为二主的想法,杀,能杀得完吗?假如我朝能喻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不分满汉,共扶大清,文人学士。皆为我用,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苏麻喇姑点点头说:“万岁圣虑极是。这是大事,奴才不敢妄加评说。但是,万岁爷自身的龙位乃第一要务。这一头顾下来了,才好去想别的事呢。”
康熙知道,苏麻喇姑说的不错。外患未靖,内忧日迫,自己的皇位正在岌岌可危。——那些远虑,都是太平天子想的事,自己当前还有更当紧的事呀!康熙沉痛地闭上了眼睛。苏麻喇姑见他闭目端坐,以为是困了,赶忙点好安息香放在熏炉之内,又吩咐宫女们将大灯撤去,只留下案上一盏绦红纱罩烛灯,这才近前请示道:“万岁爷该安歇了罢。”
“朕不用,还要再想些事。你叫她们下去,有你在这里侍候就可。你困了,自管在下面熏笼上歪着。
苏麻喇姑只好依言打发了下人,自己在熏笼旁支颐假寐。
康熙坐了一会儿,但觉百忧集结,万绪纷来:鳌拜的狂傲不法到如此地步,胆敢公然矫诏行逆,搜查大臣府邪,图谋拭君!大内侍卫亲兵虽多,但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实力,缓急可济的却寥若晨星。一眼望去,人尽可疑。虽然自己在乾清宫每日仍然接受内外大臣的朝拜,可作为至高无上的帝王,却有种“外人”的感觉。哼,这都是哄弄自己的虚热闹!佑大内城,做天子的竟不知哪是自己的安全之地,想来也真令人寒心。
他突然想到,要是诛杀鳌拜,必须在大内。因为外边鳌拜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怎好下得了手!三大殿当然不成。那么交泰殿、奉先殿、养心殿、体元殿、钦安殿、文华殿、武英殿,上书房……哪一处最佳呢?他一个一个挑着想,除了分析那里的人事,还要考虑到地貌、关防机密乃至于退路等等。突然他的脑子里一闪,想道了“毓庆宫”这个地方。他睁开眼凝视着案头上的红灯。此地宫禁深邃,又不过份冷僻,道路环回,可藏龙卧虎,是张网捕鳌的好地方。而且毓庆宫总管侍卫孙殿臣是自己的心腹,狼瞟等一干侍卫又都是死了的倭赫的朋友,这里能行!
但孙殿臣等干这种极其机密大事,他能不能像魏东亭那样心中只有朕呢!
想到此,康熙霍然而起,来到苏麻喇姑跟前。正要唤她,却听她声息恬静,知她已经睡了,便返身取了一件袍子轻轻替她盖上。哪知苏麻喇姑骤然开目,一翻身坐了起来问道,“主子有事?”
康熙压低了声音兑:“明晚,朕要见孙殿臣和狼瞟/
“孙殿臣?”
康熙坚定地点了点头。
苏麻喇姑深思了会,眼中放出光来。说道:“奴才明白,——在哪几见?”
康熙胸有成竹沉着地说:“到小魏子家去,这事你来安排,要机密!”
苏麻喇姑点点头说:“这事奴才去办,主子放心好了。”
却说在皇宫御茶房当差的小毛子把给母亲买药的钱全送进了赌场,输得干干静静又没辙了。
他是个孝子,因父亲下世得早,母亲守寡带了他和哥哥苦熬了十二年。后来,哥哥娶了嫂子,分开了过,把他和老娘闪在一旁。老娘只得给人家缝洗衣裳过日子。不料母亲上了岁数,身子骨儿就不行了。又遇上腊月天洗衣裳冻坏了双手,一到秋天骨节便肿得老粗”痛入骨髓,连缝缝补补的活也干不成。嫂子不贤,哥哥偷着接济一点:哪里养得两个活口!
正好这时,宫里要人,小毛子走投无路,心里一发横”偷偷儿净了身,挣这两吊半的月例钱来养活老娘。老娘听说后,一急之下,两眼昏黑,从此衣了瞎子。为给母亲治病,小毛子断不了从宫里偷一点小物件到鬼市上受钱。再不然仗着鬼聪明儿赌赢几个钱给老母治病。好在宫里这种事多了。大家也不以为意。今年冬季冷得特别早,眼见母亲又过不下去,自己又赌失了手,这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文表哥那里是不敢求了。虽说多少总不落空,但求一次挨一次骂,实在丢脸,况且人家也是一大家子呢。魏东亭那里。倒是有求必应,只是求的次数多了,自己也张不开口。无奈何,便溜到御厨房我厨子阿三拆兑几个。
阿三是讷谟的干儿子。他听了来意,冷笑一声道,“今儿我要扫你的脸了。我借钱给你,本钱不说,你连个利息钱都还不上,我手头也紧!你妈病了,你这算行孝,该当给的,可总不能叫我替你填这个无底洞啊?”
小毛子瞧着阿三绷得紧紧的脸,心里骂道:“什么玩意!仗着认了个干老子出入方便,你从厨房里偷摸了不少的瓷器。当我不知道。借你两个,就拿出这副嘴脸!”口里却嘻嘻笑着:“我还欠三哥十四两,在您老身上这点值甚么呀!您老再借咱几吊,下个月卖裤子我也要本利还清,如何?”
“猴儿崽子,倒有你的!”阿三笑道,“论理,不该借你,怪可怜儿的。我这还有三钱,你拿去抓药。下个月本利不清,仔细着我告了讷谟大侍卫,打你个臭死!”
小毛子无奈只得接了,出门时,见壁架上放着一只钧窑小盖碗,只有拳头大小,碗口还烧了两只绿水翼大蝉,好像在碗口吸酒的模样,显然极其名贵。不知是外头哪家臣子贡来的,他看了一下无人在意,顺手抄起来往杯里一揣便走了。阿三隔着门玻璃瞧得清楚,可是没言声。
傍晚时分,小毛子侍候了慈宁宫的水,听着阿三带了四个小厨子将没用完的御膳送乾清门赏了值夜的侍卫,等着养心殿的大监来抬了水,收拾正要回房安歇。突然见讷谟大踏步走来,忙垂手儿站好,赔笑道:“讷爷,您用过饭啦?”
讷谟铁青着面孔“哼”了一声,头也不回跨进茶具茶叶库,站在中间四下搜寻。小毛子心知不好,惴惴讪笑着掇了一张椅子来说道:“您坐着,我这就给您沏好茶。您是喝龙井呢,还是普耳?”讷谟一摆手冷笑道:“别跟我来这套!我问你,你今个在大厨房偷了什么东西?”
“大厨房?”小毛子脑子里轰然一声,脸色立时发白,强笑道:“我去三哥那借钱,敢情丢了甚么东西,那里的家什,我哪敢动得?”
“一会儿叫你嘴硬!”讷谟抬手便要打,但想想又住了手,径自开了茶顺柜,在里边胡乱翻了起来。
盖碗不在茶顺柜内,但小毛子知道不妙,若被这样乱翻,定要被寻了出来。光棍不吃眼前亏,小毛子乍着胆上前笑着拦住道:“这御茶橱是翻不得的,里边有些贡茶连封条还没有启,翻乱了老赵是不依的。”
“叭”!小毛子话音没落,左脸上早着了一掌,打得他两眼金星直冒,顿时肿胀起来。这小毛子本就泼皮无赖,哪里吃这个,回过神来高声叫道:“屎虼螂爬扫帚,你在这里做什么茧!你没瞧瞧这是你的地盘么?不过瞧着鳌中堂,叫你一声‘大爷’,你就来臭摆架子一你滚蛋,爷要出去了!”
讷谟勃然大怒:“小畜牲,别说你这儿,再难收拾的头,老子也照剃了!”骂着,左右开弓“叭叭”又是两掌。回过身来拿起桌上一串钥匙,索性打开七八扇柜门,挨柜搜查。
小毛子一屁股坐到地下,撤泼儿大哭大叫:“爷们,这是赵老爷的辖下,轮得着你么,你配么!见讷谟不理,一个劲地仍在乱翻,他真急了。灵机一动爬起来,冷不防劈手夺了钥匙跑出去,没等讷谟弄清怎么回事,“咯嘣”一声将御茶库锁了。在院里又跳又叫:
“你们都来看哪!大清朝出了新鲜事儿,讷谟大人搜查万岁爷的御茶库罗,你们都快瞧哇!黄四村,你死了?还不快找赵老爷来!”
正在用餐的乾清门侍卫,吃过饭没事的大监,听得这边又哭又喊,夹着咆哮怒骂,闹得乌烟瘴气,不知出了什么事,都聚拢来看热闹。
被锁在屋里的讷谟顿时慌了手脚,过来拉门——门锁着呢哪里拉得动!便返身去关那些茶柜门。偏生那些锁都是荷兰国进贡的,装有特制的消息儿,没有钥匙既打不开也锁不住。小毛子带着钥匙走了,哪里还关得上?忙乱中竟把左手小指差点挤断了。疼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一不小心,又把放在案上未启封的一个坛子打翻在地,“砰”地一声,茶叶撒得满地都是。外边瞧热闹的不知他在里头是怎样折腾,听了这一声儿都是一怔。
正闹着,忽听得有人喝道:“什么事大惊小叫的,成个甚么体统?”众人回头看时,却是养心殿总管太监张万强来了,便让开路。小毛子不依不饶,上前哭诉道:“张公公来了,您老瞧瞧,咱们大内里边还有个什么规矩!说着豁嘟一下打开门来。
众人瞧时,都忍不住暗笑。那讷谟真叫狼狈得很。柜子门一律都是半开半合,地下大包小包茶叶被踩得稀烂。他还右手捏着左手小指,一个劲地揉捏,痛得咬牙。见门打开,他一个箭步窜出来,把小毛子当胸一把提在半空中,便要猛下毒手。张万强忙喝道:“不许无礼!慢慢说,是怎么啦?”
讷谟哪里瞧得起张万强!拧着眉毛恶狠狠骂道:“自古太监没好人,你也不是好东西。”他还想再骂,一抬头,只见苏麻喇姑神色严峻地走了过来,知道这个宫女不同凡人,吴良辅就是因为她的一句话,被康熙下令打死的。不由得傲气先自下去了一半。撒手政开了小毛子,静等苏麻喇姑问话:
苏麻喇姑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在这时走来了呢。原来,她是按照皇上昨晚的吩咐,趁着太监、侍卫都在吃晚饭没人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换了便服的康熙送出了宫。差事办完正要返回养心殿,听到这边大吵大闹,便走了过来。见是讷谟在这逞凶,她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只是不明原因,所以不便开口说话。
小毛子一见是她来了,连忙收了眼泪上前请安,抽抽咽咽地说:“苏大姐姐,讷谟侍卫屈赖我偷东西,自个儿就来搜检。您瞧瞧他把这屋里翻成什么样子了。”
苏麻喇姑不动声色,慢慢问道:“什么东西丢了?”
“我也不知道,您问他!”小毛子指着讷谟道。
讷谟气得脸乌青,说:“他偷了一只钩窑盖碗!”
“谁瞧见的?”苏麻喇姑叮着问了一句。
“我?”站在一旁的阿三卖弄般地开了口,“我亲眼瞧得真!”
苏麻喇姑口齿极为简捷:“东西是你御厨的,你是御厨房的人,既瞧见了为什么不当场拿住?这真反了!张万强,告诉赵秉臣,革掉他!”复回头又对讷谟道:“凭你再有理,这御茶房库里放的是皇上的东西,打狗还要瞧主人呢,你怎么敢随便就搜?——你先去吧,这事明个儿再作分晓。”
“那也得瞧瞧里头有没有盖碗!”讷谟气得面色发白,有理的事被弄成这样子,实在窝囊得难以咽气。想到这儿又加一句,“那盖碗也是御用的,他偷了去,倒没有罪名儿?”
“好!”苏麻喇姑笑道,“这事我来办。查住了,一起处置!”说着便进库来。挨柜一牛件细看,小毛子的心提到嗓子眼儿上。
苏麻喇姑先把所有的茶柜一一看过,又返回茶具器皿柜,挨次儿仔细瞧,当看至最后一柜时,挪扣蝉的钧窑盖碗赫然在目。此时小毛子真是面无人色,却见苏麻喇姑伸手进去翻动一阵,又将手抽出,拍了拍骂道:“里头浮灰有二指厚,你这奴才怎么当的差!”
那小毛子正吓得一身臭汗,听得却是骂“里头脏”,忙连连称道:“苏大姐姐骂得是,我明儿好好儿整治整治!”心里却奇怪她因何不肯揭破这层纸儿。
她到别处又看看,然后走出来道:“没有找出来。你们侍卫上仔细一点,见有了时告诉我一声儿,我整治他!”说罢,竟自姗姗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