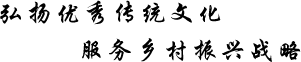第九回 丹桂园消闲观戏剧 番菜
作者:梦花馆主
且说黛玉坐了马车,直到丹桂园门前停下,早有案目过来招接。阿金搀扶了黛玉,跟着案目进园上楼,走入第三个包厢内坐下。案目放了一张戏单,又见茶房送过两碗茶、四只水果茶食盆子,方才去了。黛玉对戏台上一望,又把戏单看了一看,知已做到第三出了。阿金在旁问道:“奶奶,格出啥格戏介?”黛玉道:“格出叫《定军山》,也跟仔我看过歇格哉。”阿金道:“划一我看过歇格哉,我记性叫邱得来!”说着,用手一指,又道:“奶奶,看着黄盔甲格脚色,叫啥格名字介?”黛玉道:“格格扮黄忠格脚色,叫李兴斋,做功一点勿好。好脚色出场才勒后头得来。”
正与阿金讲话,忽闻下面人声嘈杂,不知为了何事。忙向楼下正厅上一看,见进来无数的看客,挨挨挤挤把正厅坐得满满,甚至有几个人连坐位也没有,只得退出去了。黛玉再看对面包厢里面,也与楼下差不多。却见有几个熟人在内,仔细一认,原来是李巧玲、李三三同客人在那里看戏,就命阿金去请。不一回,巧玲、三三同来,与黛玉叙话。三三问道:“黛玉姐,啥落今朝一干子勒里介?”黛玉道:“奴为仔呒心想落,所以一干子来格呀。”巧玲道:“难道杨老勿来陪格?”黛玉道:“去说俚,故歇勿比以前哉,一个月当中,有廿日天勿勒奴房里,想奴冷冰冰坐勒浪,阿要气闷煞介?难末倪格阿金撺掇奴出来看戏格呀。”巧玲道:“格倒勿怪要气闷,还是出来白相相,散散心格好。”三人略谈片刻,巧玲、三三因有客人在那边,未便久坐,即辞了黛玉,仍回对面包厢中去了。黛玉见他们已去,心中翻羡慕他们的闲散,口里却说不出来,依旧回转身躯,看那台上的戏,已做到第五出,是孙春恒、大奎官、孙瑞堂的《二进宫》。台下喝彩的声音,犹如众犬狂吠一般。阿金笑道:“啥落格种喝彩格人,才实梗穷凶恶极格佬。”黛玉笑了一笑,也不言语。又见《二进宫》完了,换了一出《恶虎村》武戏,霎时锣鼓喧天。那个扮黄天霸的武小生练了一回狠劲,与两个开花面的大战一场,打得如落花流水,足有半个时辰,方才停止,做那出《翠屏山》了。
黛玉是凝神注目,看那绣花门帘一掀,台下喝了一声彩,见黄月山扮着石秀着一身元色的短袄,手里拿着一本帐目,精神抖擞,气度从容,做那交帐的一段,唱工又好,做工又佳,把黛玉看出了神。再看扮杨雄、潘巧云两个角色,却甚平常,远不及月山。后来做到石秀舞刀一节,更觉神采飞扬,英风飒爽,所以黛玉一双俏眼直射到月山身上。却巧月山舞刀已毕,把头往上一抬,眼光射进包厢,见了黛玉的花容,未免四目传情,将眼中的光线斗了一回。但月山不认识黛玉,仅不过暗暗赞赏;况且在那里做戏,未便久视。在黛玉则情丝一缕,已把自身缚定,心里胡思乱想,忽上忽下,恨不得差阿金前去与月山通知一声,约他在何处相会,了此心愿。欲待启口,又想着有些不妥:“此事断不可造次的,究竟我已嫁了杨四,设或事机不密,弄出事来,如何是好?再者我看他的戏只有两三次,我虽认识他,他却不认识我,怎能勾搭得上?必须缓缓行事,天天到这里看戏,让他见熟了我的面,然后命心腹人去关会他,谅他断无不肯。待他肯了,再想法儿,岂不稳当?”打算方定,见那出戏已经完了,即听阿金唤道:“奶奶,倪阿要去罢,还有一出送客戏,是呒啥好看格哉。停歇出去,勿知哪哼轧法得来。”
黛玉点点头,立起身来就走,后面跟着阿金,刚走到扶梯跟首,见楼下上来一个人,对黛玉仔细观看。黛玉也瞟眼过去,认得即是黄月山,卸了戏妆,特地来看他的。阿金不知袖里,看见一个人向黛玉目不转睛,他就骂道:“格人倒少有格,还勿搭我滚开点来!看差仔人头,只管对倪呆看,阿要拨两记耳光吃吃喏!”月山听了,也不接嘴,就此走了开来。黛玉此时未便阻住阿金,只得说道:“去骂俚,倪走倪格路罢。”于是主仆下楼,觉得渐渐挤起来了,挤到门外,见自己车子停在那里,阿金喊应了马夫,方搀扶黛玉上车,一径回转家中,已是十二点钟了。
黛玉命阿金去打听今夜老爷可曾回府。少停回覆说:“老爷在左红玉家吃酒,已差人来关照,今夜住在他家了。”黛玉一听,又叹了一口气,就收拾上床安睡。这一夜的念头,不知想了多少,深恨杨四薄情,不来伴我,莫怪我暗中行事,要你背这块千斤石碑了。想了一回杨四,又想到月山身上:“我在戏园下楼之际,月山对我细看,一定有情于我。虽被阿金打岔,骂了他几句,谅无妨碍。得能成就,我何妨撇去杨四,下堂而去,与他做长久夫妻?倘杨四不肯放我,我便寻死觅活,天天同他吵闹,不怕不让我自由,任我自去了。但须与阿金说明,方好做这件事。”主意已定,便朦朦胧胧的睡去。直睡到红日斜西,始起身梳洗,略略用些点心。晓得杨四尚未归家,仍命人去定了包厢,叫了马车,专等到了晚上,用过了夜膳,依旧同阿金前去看戏,却与昨天一样,毋庸再说。
总之黛玉自此之后,无日不进戏馆,一连有二十余天。杨四虽然知晓,却并不来管他,落得耳根清静,故每天不等黛玉归来,先自去睡了。也是他们缘分将尽,所以见了黛玉,不但不爱,而且有些怕他,愈怕愈疏,愈疏愈远,这是一定之理。
我且将杨四搁过一边,单说黛玉看戏以来,已将一月,与月山久已眉目传情。月山见他夜夜到此,留心打听,也知黛玉的底细,惟两下尚未成交,因有阿金在旁,故未一通言语。黛玉知他之意,一日时将傍晚,黛玉故意问阿金道:“阿晓得,老爷阿勒屋里?如果勿曾出去,去请俚得来,说奴有闲话搭俚说佬。”阿金道:“故歇辰光板归勿勒屋里格,叫我去请,到洛里去寻介?”黛玉道:“咳,俚前日仔到奴房里转一转就去,留才留勿住,推头有事体,亦到外势去哉。阿金想想看,俚待我,实梗格薄情,真真害仔奴一世,将来勿知哪哼嗄。”阿金道:“我也勒里旁光火,老爷既呒不情,奶奶亦好呒不义,啥落是要跟仔俚过一世格介?”这两话句,是阿金有意迎合黛玉的。黛玉道:“末跟仔奴长远哉,奴格脾气,也摸得着格哉。奴待,待奴,大家总算呒啥。故歇奴有一句闲话要想搭说,总要答应奴,帮奴格忙格。”阿金早已会意,说道:“只要奶奶吩咐,我终呒不勿做格。”黛玉听他答应,立起身来,走到阿金身边,向阿金耳朵上错落错落说了几句。阿金点点头,口中只说:“容易容易,奶奶放心末哉,包弄得成功格。”要晓得黛玉说的什么话,此刻且慢表明,看了下文,自然知道。
其时娘姨已把夜饭搬了上来,黛玉唤阿金一同吃了,然后略略打扮,又换了一套衣裙,另行取出几件,送与阿金穿了。阿金直受不辞,匆匆的搀了黛玉一同上车,到戏园中而去。两人坐在包厢里面,看过了两三出,忽见黄月山立在戏房门口,身上穿的衣服甚是华丽,一双眼睛只向黛玉那边观看。黛玉情不自禁,对他笑了一笑。阿金恐他不来,也把手略招了一招,似乎说道:“来末哉,呒啥要紧格。”这个意思,月山怎么不懂?即差一个茶房,备了四样细点心,另泡了一壶好茶,送到黛玉这里来,说是我们黄老板的敬意。黛玉暗暗欢喜,就赏了茶房四块洋钱。茶房千多万谢,欣然去了。黛玉以为月山必定上楼来与他说话,那知等了一回,戏又做过了两出,仍不见来,心中有些焦躁,意欲命阿金去知会他。又恐耳目众多,被人瞧见,太不雅相,设或事尚未成,那个臭名声已先传了出去,岂不是羊肉未吃,惹了一身膻吗?正在那里踌躇,见方才来过的茶房走至黛玉面前,说道:“我们黄老板说,今天不便与奶奶讲话,明日五六点钟,请奶奶到金隆番菜馆吃大菜,我们黄老板在这边恭候,务祈奶奶要驾临的,特差我来请个示下。”黛玉听了,觉得不好意思,一时回不出口。阿金在旁代答道:“晓得哉,去回覆唔笃黄老板,明朝五六点钟,准其算数来末哉。”茶房答应了几个“是”,自去回覆月山,不须细表。仍说黛玉因此事成功,甚为得意,又暗赞月山细心,断不至走漏风声,别有后患。那知俗语有两句话说得极好,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此时黛玉那里想得到?惟有一心一意要与月山姘识,即使冒险而行,也有些顾不得了。你想这样的淫妇可恨不可恨?可杀不可杀?杨四待他不薄,件件都肯依他,有得穿,有得吃,有得用,没一样不称他的心,只欠缺些枕席上的工夫,怕他夜夜缠扰,略略与他疏淡了些。其实一月之中,未尝不应酬他数次,他即怨恨万分,背着杨四,要做那不端之事,口口声声只说杨四薄情,不说自己无情。所以我做书的深恶痛嫉,把他比作“九尾狐”,可不是冤枉了。不然,从前有个自称“老上海”的,做成一部三十年上海北里之怪历史,偏要改名叫做“胡宝玉”,其中毫无情节,单把胡宝玉比来比去,其实本传只有一小段,阅之令人生厌,又用了许多文法,有什么趣味呢?故我另编一部,演成白话,将他实事细细描写出来。虽不免有些点缀牵合而成,譬如做一本戏,除去了管弦锣鼓,如何做得成功?纵使勉强唱了几出,也与村歌野讴一般,只怕没有人肯出钱,去听这样的戏了。
闲话少叙。此时黛玉与阿金二人看月山做过了戏,仍然坐车回去。到了家中,见杨四走进房来问道:“你夜夜去看戏,怎么看不厌的,莫非新到了好角色吗?”黛玉冷疏疏的答道:“是难得到我房里格,奴一干子呒心想,只好去看看戏,消消闲,终勿能管奴勒海。”杨四道:“我并不是管你,不过问问你罢了,难道问差了吗?”黛玉道:“也来问奴,奴也勿来问。走格阳关路,奴走奴格独木桥。是有人陪伴,勿比奴冷清清,单怨自家格苦命。故歇看几本戏,也教呒法。查三问四,奴勿见得去偷人格;就是偷人,只好算害奴格,奴总勿差勒海。自家去想想看!”这几句话,把杨四气得无言可答,呆呆的坐了一回,暗想:“黛玉已变心肠,如今天天出外看戏,其中必有缘故。但未得他的把柄,我且暂时忍耐,留神察看便了。”所以强作笑容,说道:“你不要这样多心,我因为身子不好,故尔不来陪伴你,你怎么说几句话呢?”黛玉并不回答,卸妆已毕,自到床上去睡了。
杨四觉得没趣,要想走出房去,到别处去睡觉,忽然转了一个念头:“或者他尚未变心,只因一时气愤,说出这话,也未可知。我既在此,权且住宿一宵,慢慢试探,不要将事决裂,反为不美。”想定主意,把长衫宽下,在黛玉外床睡了。可见杨四并未心冷,实是黛玉不好,为贪淫欲,终嫌杨四不济,难尽云雨之欢。究竟黛玉是个贱娼,比不得人家夫妇,做妻子的无不怜惜丈夫,怎肯把丈夫斫丧了身子?若黛玉则不然,即使杨四死了,我不妨再嫁别人。存了这片心肠,还要顾怜什么丈夫呢?况现在黛玉心里只在月山身上,所以杨四上床来睡,他终不瞅不睬,朝着里床假寐。杨四落得适意,也不去叫他,直睡到日上纱窗,遂即起身去了。
黛玉初时假睡,后来真已睡熟,及至一觉醒转,见杨四已去,他又睡了片刻,方始起身梳洗。阿金道:“老爷去仔歇哉,听说朋友请去吃早饭格。倪今朝吃仔饭,阿到静安寺、申园、味莼园去白相佬?白相到五点钟,难末到格搭去阿好?勿然,等到下昼里出去,别人说起来,看戏末忒早,倒要问倪啥场化去格。”黛玉听了,甚是合意,即吩咐叫了马车,在门前伺候。一到十二点钟,用过午餐,遂同阿金上车,直到申园去吃了一回茶,又至味莼园坐了片时,挨延到四下多钟,方向金隆番菜馆来。顺便兜了一个圈子,及至到金隆门前停车,已敲过五下钟了。
阿金搀了黛玉,走将进去,早有西崽引领上楼。那西崽一头走,一头问道:“奶奶府上可是姓杨?”阿金道:“正是,问俚做啥佬?”西崽道:“现在有位黄先生,交代我问的。”阿金道:“勒浪第几号房间里介?”西崽道:“在第三号。”把手一指,又道:“到了,到了。”黛玉同阿金刚要走进,月山一见,连忙招呼,把大菜台边一只椅子拉了一拉,说声“请坐”。黛玉假作含羞,低头坐下。月山殷勤备至,说了几句羡慕的话,然后将叫人钟一揿,走进一个西崽。月山请黛玉点了几样菜,自己同阿金也各点几样。西崽答应退去,略停一停,将菜一样一样的呈上来。三人吃了一回,月山道:“少停奶奶仍去看戏,待我做过后,即来关会你们,一同到我家里去。只是屋子小得狠,未免有屈奶奶的。”黛玉低声答应。阿金道:“故歇已经七点半钟哉,阿要倪先走罢?”黛玉点点头。月山道:“确是两下走的好,奶奶请先行一步,我随后也到戏园了。”
于是,黛玉同阿金出了金隆,上车直到丹桂。见戏已开台,做到第二出了,把戏单一看,好得月山的戏排在第五出,做完时光尚早。黛玉是无心看戏,巴到第五出开场,方才有些兴致。惟这出《长坂坡》极长,足有半个时辰,始见月山进场。又换了一出花旦戏。黛玉正在观看,来了一个茶房,说道:“请奶奶走罢。”黛玉把头一点,起身同阿金就走。走至门前,见月山已在那里,把手一招,同上马车。这部车就是黛玉坐来的,那个马夫却与月山认识,预先已知照好了,故此三人都上车,即风驰电掣而去。正是:
娼妓每多淫且贱,世人幸勿爱而贪。
欲知黛玉与月山姘识后怎能出得杨家,请观下回详述。
正与阿金讲话,忽闻下面人声嘈杂,不知为了何事。忙向楼下正厅上一看,见进来无数的看客,挨挨挤挤把正厅坐得满满,甚至有几个人连坐位也没有,只得退出去了。黛玉再看对面包厢里面,也与楼下差不多。却见有几个熟人在内,仔细一认,原来是李巧玲、李三三同客人在那里看戏,就命阿金去请。不一回,巧玲、三三同来,与黛玉叙话。三三问道:“黛玉姐,啥落今朝一干子勒里介?”黛玉道:“奴为仔呒心想落,所以一干子来格呀。”巧玲道:“难道杨老勿来陪格?”黛玉道:“去说俚,故歇勿比以前哉,一个月当中,有廿日天勿勒奴房里,想奴冷冰冰坐勒浪,阿要气闷煞介?难末倪格阿金撺掇奴出来看戏格呀。”巧玲道:“格倒勿怪要气闷,还是出来白相相,散散心格好。”三人略谈片刻,巧玲、三三因有客人在那边,未便久坐,即辞了黛玉,仍回对面包厢中去了。黛玉见他们已去,心中翻羡慕他们的闲散,口里却说不出来,依旧回转身躯,看那台上的戏,已做到第五出,是孙春恒、大奎官、孙瑞堂的《二进宫》。台下喝彩的声音,犹如众犬狂吠一般。阿金笑道:“啥落格种喝彩格人,才实梗穷凶恶极格佬。”黛玉笑了一笑,也不言语。又见《二进宫》完了,换了一出《恶虎村》武戏,霎时锣鼓喧天。那个扮黄天霸的武小生练了一回狠劲,与两个开花面的大战一场,打得如落花流水,足有半个时辰,方才停止,做那出《翠屏山》了。
黛玉是凝神注目,看那绣花门帘一掀,台下喝了一声彩,见黄月山扮着石秀着一身元色的短袄,手里拿着一本帐目,精神抖擞,气度从容,做那交帐的一段,唱工又好,做工又佳,把黛玉看出了神。再看扮杨雄、潘巧云两个角色,却甚平常,远不及月山。后来做到石秀舞刀一节,更觉神采飞扬,英风飒爽,所以黛玉一双俏眼直射到月山身上。却巧月山舞刀已毕,把头往上一抬,眼光射进包厢,见了黛玉的花容,未免四目传情,将眼中的光线斗了一回。但月山不认识黛玉,仅不过暗暗赞赏;况且在那里做戏,未便久视。在黛玉则情丝一缕,已把自身缚定,心里胡思乱想,忽上忽下,恨不得差阿金前去与月山通知一声,约他在何处相会,了此心愿。欲待启口,又想着有些不妥:“此事断不可造次的,究竟我已嫁了杨四,设或事机不密,弄出事来,如何是好?再者我看他的戏只有两三次,我虽认识他,他却不认识我,怎能勾搭得上?必须缓缓行事,天天到这里看戏,让他见熟了我的面,然后命心腹人去关会他,谅他断无不肯。待他肯了,再想法儿,岂不稳当?”打算方定,见那出戏已经完了,即听阿金唤道:“奶奶,倪阿要去罢,还有一出送客戏,是呒啥好看格哉。停歇出去,勿知哪哼轧法得来。”
黛玉点点头,立起身来就走,后面跟着阿金,刚走到扶梯跟首,见楼下上来一个人,对黛玉仔细观看。黛玉也瞟眼过去,认得即是黄月山,卸了戏妆,特地来看他的。阿金不知袖里,看见一个人向黛玉目不转睛,他就骂道:“格人倒少有格,还勿搭我滚开点来!看差仔人头,只管对倪呆看,阿要拨两记耳光吃吃喏!”月山听了,也不接嘴,就此走了开来。黛玉此时未便阻住阿金,只得说道:“去骂俚,倪走倪格路罢。”于是主仆下楼,觉得渐渐挤起来了,挤到门外,见自己车子停在那里,阿金喊应了马夫,方搀扶黛玉上车,一径回转家中,已是十二点钟了。
黛玉命阿金去打听今夜老爷可曾回府。少停回覆说:“老爷在左红玉家吃酒,已差人来关照,今夜住在他家了。”黛玉一听,又叹了一口气,就收拾上床安睡。这一夜的念头,不知想了多少,深恨杨四薄情,不来伴我,莫怪我暗中行事,要你背这块千斤石碑了。想了一回杨四,又想到月山身上:“我在戏园下楼之际,月山对我细看,一定有情于我。虽被阿金打岔,骂了他几句,谅无妨碍。得能成就,我何妨撇去杨四,下堂而去,与他做长久夫妻?倘杨四不肯放我,我便寻死觅活,天天同他吵闹,不怕不让我自由,任我自去了。但须与阿金说明,方好做这件事。”主意已定,便朦朦胧胧的睡去。直睡到红日斜西,始起身梳洗,略略用些点心。晓得杨四尚未归家,仍命人去定了包厢,叫了马车,专等到了晚上,用过了夜膳,依旧同阿金前去看戏,却与昨天一样,毋庸再说。
总之黛玉自此之后,无日不进戏馆,一连有二十余天。杨四虽然知晓,却并不来管他,落得耳根清静,故每天不等黛玉归来,先自去睡了。也是他们缘分将尽,所以见了黛玉,不但不爱,而且有些怕他,愈怕愈疏,愈疏愈远,这是一定之理。
我且将杨四搁过一边,单说黛玉看戏以来,已将一月,与月山久已眉目传情。月山见他夜夜到此,留心打听,也知黛玉的底细,惟两下尚未成交,因有阿金在旁,故未一通言语。黛玉知他之意,一日时将傍晚,黛玉故意问阿金道:“阿晓得,老爷阿勒屋里?如果勿曾出去,去请俚得来,说奴有闲话搭俚说佬。”阿金道:“故歇辰光板归勿勒屋里格,叫我去请,到洛里去寻介?”黛玉道:“咳,俚前日仔到奴房里转一转就去,留才留勿住,推头有事体,亦到外势去哉。阿金想想看,俚待我,实梗格薄情,真真害仔奴一世,将来勿知哪哼嗄。”阿金道:“我也勒里旁光火,老爷既呒不情,奶奶亦好呒不义,啥落是要跟仔俚过一世格介?”这两话句,是阿金有意迎合黛玉的。黛玉道:“末跟仔奴长远哉,奴格脾气,也摸得着格哉。奴待,待奴,大家总算呒啥。故歇奴有一句闲话要想搭说,总要答应奴,帮奴格忙格。”阿金早已会意,说道:“只要奶奶吩咐,我终呒不勿做格。”黛玉听他答应,立起身来,走到阿金身边,向阿金耳朵上错落错落说了几句。阿金点点头,口中只说:“容易容易,奶奶放心末哉,包弄得成功格。”要晓得黛玉说的什么话,此刻且慢表明,看了下文,自然知道。
其时娘姨已把夜饭搬了上来,黛玉唤阿金一同吃了,然后略略打扮,又换了一套衣裙,另行取出几件,送与阿金穿了。阿金直受不辞,匆匆的搀了黛玉一同上车,到戏园中而去。两人坐在包厢里面,看过了两三出,忽见黄月山立在戏房门口,身上穿的衣服甚是华丽,一双眼睛只向黛玉那边观看。黛玉情不自禁,对他笑了一笑。阿金恐他不来,也把手略招了一招,似乎说道:“来末哉,呒啥要紧格。”这个意思,月山怎么不懂?即差一个茶房,备了四样细点心,另泡了一壶好茶,送到黛玉这里来,说是我们黄老板的敬意。黛玉暗暗欢喜,就赏了茶房四块洋钱。茶房千多万谢,欣然去了。黛玉以为月山必定上楼来与他说话,那知等了一回,戏又做过了两出,仍不见来,心中有些焦躁,意欲命阿金去知会他。又恐耳目众多,被人瞧见,太不雅相,设或事尚未成,那个臭名声已先传了出去,岂不是羊肉未吃,惹了一身膻吗?正在那里踌躇,见方才来过的茶房走至黛玉面前,说道:“我们黄老板说,今天不便与奶奶讲话,明日五六点钟,请奶奶到金隆番菜馆吃大菜,我们黄老板在这边恭候,务祈奶奶要驾临的,特差我来请个示下。”黛玉听了,觉得不好意思,一时回不出口。阿金在旁代答道:“晓得哉,去回覆唔笃黄老板,明朝五六点钟,准其算数来末哉。”茶房答应了几个“是”,自去回覆月山,不须细表。仍说黛玉因此事成功,甚为得意,又暗赞月山细心,断不至走漏风声,别有后患。那知俗语有两句话说得极好,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此时黛玉那里想得到?惟有一心一意要与月山姘识,即使冒险而行,也有些顾不得了。你想这样的淫妇可恨不可恨?可杀不可杀?杨四待他不薄,件件都肯依他,有得穿,有得吃,有得用,没一样不称他的心,只欠缺些枕席上的工夫,怕他夜夜缠扰,略略与他疏淡了些。其实一月之中,未尝不应酬他数次,他即怨恨万分,背着杨四,要做那不端之事,口口声声只说杨四薄情,不说自己无情。所以我做书的深恶痛嫉,把他比作“九尾狐”,可不是冤枉了。不然,从前有个自称“老上海”的,做成一部三十年上海北里之怪历史,偏要改名叫做“胡宝玉”,其中毫无情节,单把胡宝玉比来比去,其实本传只有一小段,阅之令人生厌,又用了许多文法,有什么趣味呢?故我另编一部,演成白话,将他实事细细描写出来。虽不免有些点缀牵合而成,譬如做一本戏,除去了管弦锣鼓,如何做得成功?纵使勉强唱了几出,也与村歌野讴一般,只怕没有人肯出钱,去听这样的戏了。
闲话少叙。此时黛玉与阿金二人看月山做过了戏,仍然坐车回去。到了家中,见杨四走进房来问道:“你夜夜去看戏,怎么看不厌的,莫非新到了好角色吗?”黛玉冷疏疏的答道:“是难得到我房里格,奴一干子呒心想,只好去看看戏,消消闲,终勿能管奴勒海。”杨四道:“我并不是管你,不过问问你罢了,难道问差了吗?”黛玉道:“也来问奴,奴也勿来问。走格阳关路,奴走奴格独木桥。是有人陪伴,勿比奴冷清清,单怨自家格苦命。故歇看几本戏,也教呒法。查三问四,奴勿见得去偷人格;就是偷人,只好算害奴格,奴总勿差勒海。自家去想想看!”这几句话,把杨四气得无言可答,呆呆的坐了一回,暗想:“黛玉已变心肠,如今天天出外看戏,其中必有缘故。但未得他的把柄,我且暂时忍耐,留神察看便了。”所以强作笑容,说道:“你不要这样多心,我因为身子不好,故尔不来陪伴你,你怎么说几句话呢?”黛玉并不回答,卸妆已毕,自到床上去睡了。
杨四觉得没趣,要想走出房去,到别处去睡觉,忽然转了一个念头:“或者他尚未变心,只因一时气愤,说出这话,也未可知。我既在此,权且住宿一宵,慢慢试探,不要将事决裂,反为不美。”想定主意,把长衫宽下,在黛玉外床睡了。可见杨四并未心冷,实是黛玉不好,为贪淫欲,终嫌杨四不济,难尽云雨之欢。究竟黛玉是个贱娼,比不得人家夫妇,做妻子的无不怜惜丈夫,怎肯把丈夫斫丧了身子?若黛玉则不然,即使杨四死了,我不妨再嫁别人。存了这片心肠,还要顾怜什么丈夫呢?况现在黛玉心里只在月山身上,所以杨四上床来睡,他终不瞅不睬,朝着里床假寐。杨四落得适意,也不去叫他,直睡到日上纱窗,遂即起身去了。
黛玉初时假睡,后来真已睡熟,及至一觉醒转,见杨四已去,他又睡了片刻,方始起身梳洗。阿金道:“老爷去仔歇哉,听说朋友请去吃早饭格。倪今朝吃仔饭,阿到静安寺、申园、味莼园去白相佬?白相到五点钟,难末到格搭去阿好?勿然,等到下昼里出去,别人说起来,看戏末忒早,倒要问倪啥场化去格。”黛玉听了,甚是合意,即吩咐叫了马车,在门前伺候。一到十二点钟,用过午餐,遂同阿金上车,直到申园去吃了一回茶,又至味莼园坐了片时,挨延到四下多钟,方向金隆番菜馆来。顺便兜了一个圈子,及至到金隆门前停车,已敲过五下钟了。
阿金搀了黛玉,走将进去,早有西崽引领上楼。那西崽一头走,一头问道:“奶奶府上可是姓杨?”阿金道:“正是,问俚做啥佬?”西崽道:“现在有位黄先生,交代我问的。”阿金道:“勒浪第几号房间里介?”西崽道:“在第三号。”把手一指,又道:“到了,到了。”黛玉同阿金刚要走进,月山一见,连忙招呼,把大菜台边一只椅子拉了一拉,说声“请坐”。黛玉假作含羞,低头坐下。月山殷勤备至,说了几句羡慕的话,然后将叫人钟一揿,走进一个西崽。月山请黛玉点了几样菜,自己同阿金也各点几样。西崽答应退去,略停一停,将菜一样一样的呈上来。三人吃了一回,月山道:“少停奶奶仍去看戏,待我做过后,即来关会你们,一同到我家里去。只是屋子小得狠,未免有屈奶奶的。”黛玉低声答应。阿金道:“故歇已经七点半钟哉,阿要倪先走罢?”黛玉点点头。月山道:“确是两下走的好,奶奶请先行一步,我随后也到戏园了。”
于是,黛玉同阿金出了金隆,上车直到丹桂。见戏已开台,做到第二出了,把戏单一看,好得月山的戏排在第五出,做完时光尚早。黛玉是无心看戏,巴到第五出开场,方才有些兴致。惟这出《长坂坡》极长,足有半个时辰,始见月山进场。又换了一出花旦戏。黛玉正在观看,来了一个茶房,说道:“请奶奶走罢。”黛玉把头一点,起身同阿金就走。走至门前,见月山已在那里,把手一招,同上马车。这部车就是黛玉坐来的,那个马夫却与月山认识,预先已知照好了,故此三人都上车,即风驰电掣而去。正是:
娼妓每多淫且贱,世人幸勿爱而贪。
欲知黛玉与月山姘识后怎能出得杨家,请观下回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