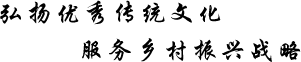第十七回 胡涂虫受赃枉断
作者:竹秋氏
却说沈伍氏骂走了祝自新,又得了一千两银子与多少东西,好不畅快。惟有兰姑心内大为不怿,专望他父亲回来。恰好这日沈若愚已抵扬州,将布匹交代店中,回家一行。伍氏母女迎接入内,兰姑舀水与父亲洗脸,又送上茶来。若愚问及家中近况,兰姑未待伍氏开口,即问道:“嘉兴有个姓祝的住在苏州,与我家上代通家世好,前日在苏州会过几次,父亲曾托他带了一封银子来家,可有此事?”沈若愚笑道:“你们的话我一句不解,我在那里会过姓祝的?又何尝托他寄带银信?我每月薪俸若干,你们是晓得的,何能成封的向家里寄,我又不曾做强盗打抢去。你们不是活见鬼么?”伍氏听了,今日方明白过来,遂将祝自新如何假冒世交,如何借住,如何被他骂走的话,细说一遍。沈若愚怒道:“岂有此理!你不晓得是个女流,家中又有年轻的女儿,乱把陌生人留住来家。只凭他满口虚词,你即信以为实。而今受了他糟蹋,以致兰姑吃了亏苦,只怕将来你这个人,还要被人骗去。”说得伍氏恼羞成怒道:“他说与我家世交,又有银两寄回,他说得千真万确,我才相信的。如今人已被我骂走,你宝贝女人,油皮都未擦去一块,还落了许多银子下来,算起来都是我的造化。若单靠你终年巴巴结结,不知累到临死,可有这宗成等的银钱。你不感激我,反啰哩啰嗦的埋怨人,不是老霉了么!”
兰姑见父母斗口,又听母亲的话说得不堪入耳,怕邻舍闻知传为笑柄,忙上前劝谏。伍氏忿忿的回后去了,不理他丈夫。沈若愚气得浩叹道:“你母亲若大年纪,作事全没道理,真是个无见识贪小利的妇人,以致累我儿受辱。日后我再远出,如何能放心呢?我也愁那姓祝的平白丢下许多银物,未必善肯干休。明日待我访问他可仍住在对门,将银两物件全数退还了他,当面教训他一场,以免后患。况且这宗不义不明之财,我也不屑要的。只怕你母亲恃蛮,不把银物交出,又要淘气。”兰姑道:“父亲此举甚善,少停待女儿婉言相劝母亲,再开陈利害,想母亲息了气,都可应允。”
父女正在堂前议论,忽听打门甚急,兰姑恐有客至,走了进去。沈若愚出来开门,见是几个公人装束,忙止住道:“诸位何来,寻谁说话的。”张政道:“你家可姓沈,你可是沈若愚老爹么?”若愚道:“不错。”王洪道:“我等特来奉拜的。”若愚关了门,邀着众差入内坐下,问道:“诸位是那座衙门里来,寻我有何见谕?”王洪道:“小〔的1衙门是甘泉县,因敝上胡太爷有件公事在此,请老爹过目。”说着,在身边取出朱签递过,若愚接过看毕、,大怒道:“这才真真是平地起风波,无影无形的含血喷人。不瞒诸位说,银子有一千两在此,是他无中生有骗信了内子,留他住在舍下,后来因他干出没廉耻的事,无颜对人,又怕我回来见了面更下不去,他即连夜遁走,丢下这宗银子未及取去。我适才正打算退还他,不料他先捏词告我。若说我当面把女儿卖与他作妾,更是笑话,我连认都不认识他。不劳诸位费心,既然我今日回来,无用内子与小女到案,我去当堂与祝自新质个明白,孰是孰非。请诸位少坐,容我进去说知内子等人,即随诸位同行。”张政道:“你老爹做事真称爽快,请到后面吩咐一声,我等在此拱候。”若愚起身入内,对伍氏说,祝自新如何谎告了他。“你们不要害怕,我随差人去审官司,看那小畜生如何说法,真是真假是假,自有公论。快把那一千两银子取出来,我要带了去。”伍氏闻说,很吃了一惊道:“这是那里说起,也亏他忍心撒这样大诳。”兰姑含泪道:“我说姓祝的必要播动是非报复前怨,果不出我所料。只愁他官官相护,父亲须要见机而作为是。”若愚道:“你又多虑了,我本是清白人家,怎能卖起女儿来?难道凭他一面之词,县官即信为实事么?试问我女儿卖与他为妾,有何见证,有何凭据?”兰姑道:“他既饰词谎告,必有一二处使官府相信才可准的状词,父亲不可不防。”若愚点头道:“我都知道,临时自有处置。”伍氏已将银子搬出,若愚取了方布裹好,提在手内,出来同着众差去了。
伍氏关好门户,愈想愈气,顿足大骂道:“祝自新,我把你这天诛地灭,千剐万剁的小畜类,你调戏了人家女儿,反告人昧你银子,不卖女儿与你。只恐你家老婆,日后也要卖与人做小的。”兰姑坐在一旁,不发一言,心如刀割。细想这件事情,“怕的父亲要吃亏苦,一则父亲为人憨直,平空冤枉了他,恐出口即挺撞了县官;二则祝姓既思发手告人,必然安排停当,甚至连身纸等据都可伪造,况他又是个缙绅子弟,难免与县官有旧,若再通了贿赂,分外可虑。”惟有默祷神明保佑他父亲,平安无事回来。又与伍氏商议,央了邻人至县前听信。
不说母女在家愁闷。单说沈若愚到了衙门,张政将他押入班房,派王洪同伙计看管。自己到宅门上来,回说:“被告若愚,今日回家,伍氏母女可不赴案,已将沈若愚带到,请太爷升堂。”宅门进去回明了。少顷,传话二堂伺候。胡武彤入了公座,先唤祝绅家属王德问了一遍,吩咐跪在一旁,方唤沈若愚上来道:“沈若愚,你既将女儿卖与祝乡宦为妾,收过他五百两银子,又立了卖身文约。怎样你妻子伍氏,把祝绅的一千银子骗到了手,陡起图赖的心肠。你想祝家白白丢了一千五百两银子,算是受了你夫妻的骗了,他怎肯干休?如今告到本县衙门,本当办你个通同抵赖,姑念你远在苏州,是你妻子昧良,与你无涉。你好好把女儿送到祝绅家,祝家有了你女儿进门,他断然不记前恨,定要看顾你。你自要明白呀!”沈若愚听罢,叩首道;“真真祝自新冤枉煞小人了,莫说小人家系世代书香,纵然饿死也不肯卖女儿。就连这祝姓,小人都不认识。总怪小人妻子一时胡涂,听信他巧语花言当成真实。他又百般央求,要借住在小人家内,因他夤夜调戏了小人女儿,被小人妻子怒骂一顿,他无颜连夜走了。若说那一千银子,是他住在小人家内,他说外面不便收存,交代小人妻子与他收好。后来他遁去未及携带,丬:非什么身价,他是借此生端的。小人已将银两带来呈堂,请太爷饬祝家收领。至于他所告之词,尽是一派胡言,无半字实情,要求青天太爷做主,先问他个诬栽良民的罪才是。”
胡武彤哈哈大笑道:“沈若愚,本县看你人倒老实,像个忠厚模样,不知道你还讲几句巧话儿搪塞本县,真是人不可貌相。你既说有这一千两银子在你家内,足见祝绅不是冤栽你了。你收过人家银子,又立了文约,想不把女儿交代人家,于理上就说不去。即如将银子退与祝绅,你家妻子无故图赖人银两,又无故的辱骂人,这时候退银子,祝绅都不愿意;你何妨当初不收他银子,如今悔了约,祝绅也无可如何。只怪你做错了,本县是格外加恩,不究前情,你不要自己胡涂,自讨没趣。”
沈若愚听胡武彤句句皆袒护着祝姓,不禁心内火发,那里按耐得住,大声道:“太爷吩咐的话,叫小人死不暝闩。那祝自新有意借端栽害小人,诬良作贱,显而易见。即作他交代小人家银子一千两是有的,小人妻子不合收他银两,不把女儿交出,何以他在苏州只会见小人,又没有见过我女儿何等样人,单凭小人要卖女儿的话,他即兑付五百银子,天下那有这等痴子?再者他的五百银子是由何人交代小人的,不能一千多银子的大事,可以对面讲说的么?就是媒婆,也该要有一名,难不成小人晓得他要买妾,亲自上门去打合他的?况这一张身纸又不是小人笔迹,他既可以诬告,即可假立凭约。此数事彰明较着,要求太爷详察。”一番话,把胡武彤抢白得瞪眼无辞,羞变为怒,将惊堂一拍道:“好大胆忘八蛋,你串同你妻子图赖祝绅银两,昧不交人。本县好意开豁你,只叫你交出女儿,不来办你,还敢强词夺理挺撞本县。先打你个犯上不敬的二十个嘴巴子,再究你昧银匿女的罪。”两旁隶役齐声吆喝,走过三四名粗汉,不由分说把沈若愚拖了下来,如鹰抓燕雀一般,一五一十的掌了二十个嘴巴,打得两腮红肿,口角涔涔流血。沈若愚也不要性命,碰头顿脚的叫起极天冤屈来。胡武彤连连拍案道:“了不得,了不得!你们看这东西可恶不可恶,竟敢在本县堂前肆行无忌。把他押下去,限他三日内交人;这一千银子暂行寄库,俟他交人后仍饬他领了去。”说毕,即起身退堂。原差带了沈若愚下来,交外班房管押。
那听信的邻人如飞回来,对伍氏母女细说堂上如何审问。把伍氏吓得痛哭不已道:“这是那里来的晦气,撞着这瘟官也不问个真伪情由,一味的听信姓祝的话,反打起我家老爹来。我要这条命何用,不如到县前击鼓喊冤,与这瘟官拚了罢!不然我也对不住我家老爹,祸是因我而起的。”兰姑泪纷纷的道:“母亲,你要到县前喊冤,你即喊死了,他也不理。莫若到府里告他一状,告他个问官不明,看他怎样担当得起。”伍氏道:“用得,用得。”忙去央人写了状词,递进府内,又亲到班房里嘱咐若愚,勿用着急,且候府里批示如何,不能府里也像这瘟官胡涂虫。过了一日,府里挂出批来,仍饬甘泉县明白覆讯。
谁知这府官姓毛,即是前任上元县升任到此。刘蕴访得伍氏告了府状,他本与毛知府有交,前次在南京曾托他办过聂家姊妹的。刘蕴与祝自新商议,又备了若干黄白货物,刘蕴亲去拜会,通了贿赂。这毛知府亦是个爱财的人,答应了刘蕴,落得做个好人仍饬甘泉县覆讯,是只受其利,不计其害。胡武彤奉了府文好不得意,又提沈若愚到堂责打,再限三日交人,若仍崛强,定然重究。
伍氏母女得了信,如掉入冷水里相似。实指望府里代他昭雪此案,不料仍发在这瘟官手内,反累了若愚受责。伍氏又要去拚命,兰姑道:“母亲,这不是拚命的事,都要设法救出父亲才是。既然府里不问,难道除了他就没有别的衙门去告状么?我们这地方本系江都县管辖,闻得江都陈太爷是个清正之官,到任以来很干了几桩为民除害兴利的事。因他上省去了,才撞在那瘟官手内。过数日他都要回来的,母亲再去告他一状。若仍是不问,拚着性命去控上状,不怕姓祝的有通天手段,都要拖倒了他。”伍氏称善,只得等江都县回来告状;又愁三日限满;丈夫仍要受责。
恰恰才到两日,打听得江都县今日回衙门。伍氏如半天里得月,忙取了一方乌帕扎在头上,把状词揣在怀内,前去拦舆喊禀,较之投文候批快得多呢!陈小儒轿子将要进衙,伍氏突出叫冤,小儒收了状词,细看情由,不由怒从心起道:“胡礼图太胡闹了,怎样只凭原告一面之词,硬派沈家女儿是卖与他的,也不问个是非曲直。可笑连毛公都胡涂起来,我怕其中定有关节。这沈家本是我该管地方,理宜归我衙门审问。”一面将伍氏暂交官媒看管,一面入衙备了移文,至甘泉县提取原被告人证,及吊核原卷。
胡武彤接着江都移文,大大吃了一惊。知道小儒是个铁面无私的人,非府尊可比,可以颟顸了事。他既回来,被告又在他衙门告发,又是他的汛地,何能不归他承审。倘一经问出祝姓诬告,岂非连我都有处分,左右思维毫无主见,只得把人证原卷先交代了江都来差。自己忙坐轿去会祝自新,叫他赶紧设法料理,不然彼此多有未便。
祝自新前在南京,亦深知小儒利害,急得抓耳挠腮,连呼不妙。刘蕴道:“陈小儒人却古怪,幸喜我与他同年,平日又有一面之交,不若待我去撞个木钟,恳他的情分。但是此人只可以情缚他,却不可以利惑他。一来他是个有家,二来他又是个临财不苟的人。拚我屈了身分去求他,料想他亦不好十分推却。”祝自新听了,连连作揖道:“我真正忘却你与陈公是同年了,即请你去走遭,不可迟缓。虽说是小弟惹下来的祸,也是你仁兄引起头的。”
胡武彤闻刘蕴去见小儒,亦大为喜欢,从旁怂慂道:“难得刘太史与陈公有年谊,只要说得入彀,他纵然开豁了沈若愚,都不致认真追究到祝贤弟身上来。刘太史既与贤弟盟好,断不可坐视不闻。古云:唇亡则齿寒。如说平了此事,连小弟都感激不尽。”你一言我一语逼得刘蕴不容不去,道:“我去是定去,至于行止我却拿不稳,若是别人,不用我去也可成功。”回头叫家丁预备轿子,到县里去拜会。胡武彤又说:“事宜从速,怕的人证到了他衙门,随时即要审问。”仍再三谆嘱了刘蕴几次,方才回衙,还心内悬悬的,候刘蕴回来消息。
少顷,轿子已至,刘蕴穿换公服,带了两名跟随,向江都县来。到了县前,先投了帖进去。小儒正坐在上房与方夫人闲话,说到沈家一案其中定有情弊,好在俟人证提到一讯即知底细。见双福上来回道:“南京刘太史要面会,有要话相商。”小儒看了帖道:“这个宝贝又到扬州来何干?我也无闲会他,你说我沿途受风,不能见客。改日过去谢步,有话再议。”双福去了,少停又上来道:“家人去回复他,他立意要见,硬下了轿坐在花厅上呢。”
小儒无奈,只得出来。刘蕴见面即抢步上前,深躬道:“治生甫至扬州,即闻口碑载道,士庶同称,足见父台恩泽周施。今日探得驺从已回,特专诚晋谒聆教,岂意拒绝太甚,不容一见,想治生多有得罪之处,深为惶恐。”小儒笑道:“仁香兄太谦了,我辈通家年好,言不至此。小弟实因沿途染受些江风:懒于酬对,尚希原谅,容改日登阶谢咎。”刘蕴连称不敢。小儒问道:“年伯老大人足疾可全愈否?”刘蕴欠身答道:“家君足患近日尤甚,医家说是壮年在边省染了山瘴疠气,刻下精力就衰,不能制伏,是以发作起来。纵能调治,都难免偏枯之患。家君仍想医治如恒,进京供职,以残喘报答圣恩。不料心强足违,深以为憾。”又问了问小儒任内的蹊径,遂道:“治生有一事奉乞,都望老父台作成。”即将祝自新告沈家的话,巧言粉饰说了一遍。又道:“敝友祝某非一定要与沈家为难,皆因此事太难为情。他不交出女儿也还罢了,怎样反诬控祝某?况祝某亦系前科副车,是个名教中人,安肯作此违法之事?沈家既不愿女儿与人作妾,祝某亦不能强逼其卖,但要把那以良作贱的事辩明。如沈家认了诬,再将一千五百银子身价退出,祝某即可罢讼。因他是个在案人证,不便干谒。特央治生过来奉求老父台推情,想老父台洞见万里,定不以治生为饰词入告了。”
小儒听刘蕴一派巧言,明知虚浮,“果然祝姓情真理直,又何用托你来致意?”即至听到说祝某系前科副车,忽然触起机来道:“令友祝某莫非即是祝道生么?”刘蕴正说得娓娓入听,不防备小儒问这一句,一时转不过口来,含糊应道:“未知是与不是,治生只知他名自新。”那脸上不禁现出忸怩〔之〕色来,小儒顿时明白,也无须追问,冷笑道:“祝道生我久闻其名,久仰其人,不用仁香兄细嘱,小弟自会关切他,定不负尊托便了。”
说毕,举茶让客,不耐烦与刘蕴多谈,催他起身。刘蕴见话不投机,也难久坐,即作辞出来。回至寓内,祝白新接着,即问道:“其事若何?胡君那边已打发两三起人来问信。”刘蕴因在祝胡二人面前,夸口小儒与他同年至好,一说必从。此时如说出真话来,怕他们要取笑他,只好随口答道:“陈公已应允了,非独重究沈家诬告,还要把他女儿判断与你作妾,叫你不可忘却了他的情分。”祝自新听了,喜得拍手顿足道:“只要他要我为情就好说了,我愿加倍馈送,但求于事有济。”即将刘蕴的话,对胡武彤家人说明,“请你家太爷但放宽心,陈公处刘太史已说通了”。来人去了,祝自新又嘱咐王德,明日赴审小心,须仍照前番说法,不可改变。“你但听陈公口内所问,依着他的口风回就是了”。欢欢喜喜的叫人买了多少酒肴,与刘蕴对饮,专候明日小儒判断。
单说小儒送出刘蕴,回至书房内,暗暗作恼道:“祝道生那畜生,前次在南京与畹秀等作对,把伯青功名都拖累去了。而今-他更名又重新捐纳前程,该应天网恢恢,又至扬州与沈姓争讼,显见他倚势凌压沈家,逼他女儿为妾。不知怎样做成圈套,将一千多银子硬栽在沈家。难得犯在我手内,若审实了他是诬控,必当从重究办,也替伯青报复那一口闷气。”又把原卷取过,细加详阅,心内早有八分了然。
到了次日黎明,升坐大堂,先将原告沈伍氏唤上,问了一遍,吩咐退下。又将沈若愚唤过,细问情由。若愚叩首道:“青天太爷,小人虽习布业,祖父都是学校中人,因小人不肖,未能读书上进克绍箕裘,才改做了买卖。虽然亦是安分清白人家,纵一贫如洗,也不忍把女儿卖人作妾,玷辱家声。何况这祝姓,小人与他向无半面,焉能远在苏州即将女儿出卖,又何以知道他要买妾?他亦安能只凭小人口内之言,即先兑五百两银子?倘若小人没有这个女儿,托言哄骗,他也相信么?再者小人既想赖他银两,何必前日当堂呈缴那一千银子,不如抵赖得毫厘全无,岂不干净?这皆系小人实情,求青天太爷详察。”说毕,连连叩首,小儒亦吩咐他跪在一旁。唤上王德道:“你家主控告沈姓吞银昧女一案,你家主怎样认得沈姓?沈若愚又怎样即将女儿出卖?你须从实细讲,不许半字撒谎。”
王德道:“小的家老主人与沈姓本有交情,并常通往来。后因老主人远出作宦,才算隔绝。日前沈若愚至苏州贩布,在茶坊内偶与家主同桌,谈及上代交谊,甚为相契。家主说因无子要到扬州买妾,问沈若愚久在扬州可知有什么出色的女子。晚间沈若愚即来寻找小的说,闻得你主人要买妾,预备多少身价?小的说只要人品好,我主人合式,一千八百都不吝惜。沈若愚说,我亲生有个女儿,名叫兰姑,今年十七岁,头脸脚手各式皆好。你主人如能出一千五百银子身价,我即定卖与他。但是我与他世交,不好出口,烦你善言为我说成,当重重酬谢,并允定小的事成之日,送小的五十两银子。小的说,你沈老爷的令嫒自然是不得批评的,只恐我主人碍于世交,不敢要你令嫒作妾。沈若愚又再三嘱托了小的数遍,小的即将此言禀知家主。家主始而不行,说我与沈家世交兄弟,何能买他的女儿,要被万人唾骂呢。后来家主被小的劝解说,我看沈老爹目下光景甚窘,亦是出于不得已才肯卖自己女儿。也因我家能出若干银子,又知道驭下宽厚,他女儿可得其所。家主听了小的话,方肯允行。随后沈若愚又亲与家主商量,他东家的本钱被他用空了若干,可能先兑些身价与他弥缝亏空?若恐无凭,我先将卖身纸写送过来,那其余银两,待我女儿过门再行兑付。家主见他说得恳切,又念他是个老实人,故而推诚腹心,先兑了了百银子,沈若愚写下一纸女女儿文契。家主因要先赴扬州,嘱沈若愚写了家信,好至扬州接他女儿,免得日后往返。到了沈家,伍氏看了信亦无异言,当〔即J对家主说,你是我家女婿了,何必住在外面,不如搬至我家来住,也省些客寓用度。二来你即可招赘我家,因我女儿自幼锤爱,我舍不得他远行。今日卖他也是出于无奈,你入赘个十朝半月,让我看看也可放心。家主听他说得有理,即移居他家,择定五日后招亲。次日就将一千两银子,兑交清楚。不料伍氏陡起不良,得了银子,翻转面皮,说家主以良作贱,逼他女儿为妾。伍氏不肯交出女儿,要想悔亲也还罢了,因家主本不愿要他女儿,是受沈若愚蛊惑而成,却不能白白丢了一千多银两,又担个逼良的声名。恰恰沈若愚由苏州回来。家主与他理论,他和伍氏一样的话,足见是预先串合的。家主气极才在县里递禀,沐胡太爷恩断,看破他夫妇伎俩,限三日内交人。伍氏又谎捏情词,在府里与太爷衙门控告。小的所说,句句是实,不敢半字增减。请太爷追究,沈若愚或交原银,或交他女儿,总要有个着落。”小儒点首微笑道:“据你所云,这沈若愚实属可恶,确是个千刁万恶的人,即活活打死,也不足以蔽其辜。但是他写卖身纸的时候,你可亲眼见着没有?”王德道:“沈若愚写契是当着家主与小的面前,亲笔写的,怎么小的没有看见?”小儒道:“既然当着你主仆写的,是他亲笔无疑了。然而本县其中有一处未解,倒要问你。沈若愚兑付五百银子,却写了一千五百银子的契。那一千银子,据你说待他女儿过门方兑,难道沈若愚不怕你主人存了歹念,赖他都付过了?沈若愚应该在契上批注明白,先兑了五百。这是天下人之恒情,他亦五十多岁的人,就该知道这情节,为何他胡里胡涂,就拢统写了?在本县看,沈若愚名虽若愚,恐愚不至此。我疑惑这张契并非是他亲笔所写,乃旁人代他写的,他反受了人家愚弄了。”王德正信口撒谎,讲得活灵活现,不提防小儒在夹缝里问这一句,一时转不过机来,回答不出,急得满脸紫涨,不由口内支吾好半晌,方勉强道:“沈若愚亦因家主是个正经人不须防备,所以才如此写的。好在家主未曾骗他,是他骗家主的。”小儒见王德形色仓惶,心内分外了然,哈哈大笑道:“好个正经人不须防备,你可知沈若愚就吃的这个苦。”顿时反过脸来,把惊堂一拍道:“好大胆奴才,你敢在本县堂前造言生事,帮着你主人害人,你不是助桀为虐么?那沈若愚就与你主人是至亲骨肉,既写到笔据,断无收五百银子肯写一千五百两的文契,天下没有这样痴子。你这该死的奴才,你主仆把沈若愚当做痴子,还来把本县当痴子看待么?代我拖下去结实打。”两边隶役一声吆喝,走过三四个人,把王德揪下。
王德大喊道:“太爷不要打钳了人,没有见过不打骗人的人,反打受骗的人,真正冤枉不浅。”小儒冷笑道:“本县今日偏要错打了你,冤枉了你,拚着你主人去告上状。你须知本县这里,非胡太爷堂上可比,容你胡言乱浯栽害平民。胡太爷是看你的主人情面,本县是玉洁冰清,一尘不染,怎容你这种样子。”说罢,又连声喝“打!”隶役等早将王德拖翻在地,褪下底衣,两个人按住他头脚,一个人举起竹板,用力的朝下打。才打了五板,早巳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因王德自幼跟随尤鼐在任,虽非姣生惯养,亦是享受不尽的人。后来尤鼐卸事,分派伺候仙女婿祝自新,又倚为心腹,除专办外差,平时还有两名三儿服侍。他如何受得起县堂上的刑法,似杀猪一般喊道:“青天太爷,青天菩萨,小的情愿招认了。”小儒止住隶役,放了王德起身,穿好裤子,遂将祝自新与刘蕴如何想谋沈家女儿作妾的话,一一承认。
小儒命招房录了他口供,道:“你主仆做得好圈套,平白地陷害良民,该当何罪?”叫原差带他下去。唤过沈若愚、伍氏道:“你的冤枉,本县已代你问清了,与你夫妇毫无干涉。但是你妻子伍氏,年已半百的人,怎样一点见识没有?皆因妇人家好贪小利,以致丈夫受累。若非本县细心详察,你夫妇真要屈死。以后处世,须要仔细。”。
沈若愚,伍氏朝上连连磕头,如捣蒜相似,齐道:“小人夫妇蒙太爷高厚之恩,雪明冤屈,惟愿太爷高升极品,万代朱衣。”小儒即当堂销案释放,沈家夫妇又叩了几个头,欣然回家去了。到了家中,兰姑见父母双双皆回,急问情由。伍氏将前后的事细说,父女三人甚为感激3当立了长生禄位,朝夕焚香,惟祝恩官早早飞升。
小儒在堂上又点了两名差役,给了堂签,吩咐他到祝自新寓内,提取本人赴案,须要小心。”两名差役退下,即向祝自新寓内来。祝自新因王德去候审,心内悬悬,坐在寓中待信。刘蕴知中有变故,瞒着祝自新悄悄上街去了。两名差役见了祝自新,将堂签收过,假说“本县太爷,现在已审确,沈家昧女吞银是实。他女儿已提到了堂,请你去具结领人”。祝自新听了,喜出望外。刘蕴又不在家,也无人计议,而且昨日说通关节,谅必此事真实不虚,忙换了衣冠,坐轿来至县衙头门外下轿。两名差役领着他上了大堂。
祝自新抬头见小儒坐的是大堂,沈家人影儿都没得半个,又见王德愁眉苦脸的躺在阶下,明知有了变故。又听两名差役唤道:“祝自新带到当面。”祝自新更外着忙,不由心内一阵乱跳,又不能退回,硬着头皮上了堂阶,跪下道:“职员祝自新见父台请安。”小儒淡笑道:“祝道生,你何时更名自新报捐的?”祝自新听得问他的前事,又直呼他的原名道生,早经神不守舍,面上失色道:“职员是祝白新,不是什么祝道生,敢是父台认错了!”小儒道:“本,县前住南京即闻你的大名,如轰雷灌耳,岂有认错之理。本县此时也不及问你更名不更名,朦捐不朦捐。你所控沈家一案,你抱屈家丁王德有一纸口供在此,你且看来。”说着,把王德的供单,掷在祝白新面前。
祝自新拾起看毕,早吓得魂飞云外,魄散风前,暗自恨道:“多怪我用错了王德,这奴才怎么就招认了,岂非要坑杀我?”
再偷觑小儒,见仙端坐堂上,铁铮铮而门,令人害怕。欲待辩白几句,王德已招承了,辩也无益,徒然自取羞辱。只得俯伏在地道:“职员一时胡涂该死,职员知罪了。尚求老父台格外施恩,笔下超生,职员愿甘责罚。”小儒道:“你也知道自己罪名?你还知道你好朋友刘仁香靠不住,他也配向本县讨情么?而且本县两袖清风,既不受人贿嘱。你只好自怨将冰山当做泰山了,你候着详办就是了。”即吩咐两名原差将祝自新领下,交官寓看管王德发外班房监押,“均候本县通详究办”。小儒起身退堂,原差带了祝自新主仆下来。
自新望着王德,顿脚道:“你怎么害了失心疯,把真情都招认了?现在怎么得了。”王德道:“还说了不了,都上了刘蕴那靟养的当。他又未曾说通,我白白地挨了五板,更冤枉呢!我们都不要怨人,只好怨命,该应碰见倒灶鬼。我细想都不派死罪,不过枷打,等我出来了,拚着把刘蕴斲死了,抵他的命。”祝自新亦深为懊悔,痛骂刘蕴。这刘蕴至晚始回寓内,打听得祝家主仆都押起来了。又恐累到自家身上,连夜溜走,也不敢回南京,至别处躲避去了。胡武彤早得了信,急得双脚一阵乱跳道:“完了,完了!我这甘泉县被他们拖掉了,偏偏在收漕的时候,这不是劫数吗!”赶忙坐轿上府,面见毛公,叩求设法。毛公道:“老兄这件事,你也怪不到我。沈伍氏来喊府状,我仍发你衙门审问。你既知道他有胆量告府状,就不怕他去控诉该管的江都县么?即不然,去告了上状,也是累赘。老兄你太任意了,若江都详了上来,我也无力回护。倘或在别人手内还有通融,陈小儒我与他世交至好,他的古怪脾气我巳尽知,他是个反面无情的人。何况目下宪眷甚隆,又保了卓异上去。老兄你不要连我这知府带掉了罢。”胡武彤见毛公都畏惧小儒刚正,格外着急,晓得求他也没用,起身作辞,回来坐在衙门愁闷。
小儒退了堂也不回上房,即下了签押房,连夜叙了通详文书,申详各处。却未提及刘蕴,到底还念同年分上,而且此次他实系因人成事,可以原谅。沈家诉词亦未波及到他身上,便宜了他罢。到了次日,一面详禀各上司衙门,将祝自新更名朦捐,列入首款,使他罪无可逭。又亲自坐轿上府来见毛公,且探一探毛公虚实。遥想此案,他既与刘蕴有旧,刘蕴竟敢来说我入彀,岂有不往说毛公之理。他多该纳贿知情,旁敲侧击他几句,叫他也存个害怕的念头,可以警戒下次。一路上想定主见,已及府衙,投入手版。未知毛公见与不见,见时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兰姑见父母斗口,又听母亲的话说得不堪入耳,怕邻舍闻知传为笑柄,忙上前劝谏。伍氏忿忿的回后去了,不理他丈夫。沈若愚气得浩叹道:“你母亲若大年纪,作事全没道理,真是个无见识贪小利的妇人,以致累我儿受辱。日后我再远出,如何能放心呢?我也愁那姓祝的平白丢下许多银物,未必善肯干休。明日待我访问他可仍住在对门,将银两物件全数退还了他,当面教训他一场,以免后患。况且这宗不义不明之财,我也不屑要的。只怕你母亲恃蛮,不把银物交出,又要淘气。”兰姑道:“父亲此举甚善,少停待女儿婉言相劝母亲,再开陈利害,想母亲息了气,都可应允。”
父女正在堂前议论,忽听打门甚急,兰姑恐有客至,走了进去。沈若愚出来开门,见是几个公人装束,忙止住道:“诸位何来,寻谁说话的。”张政道:“你家可姓沈,你可是沈若愚老爹么?”若愚道:“不错。”王洪道:“我等特来奉拜的。”若愚关了门,邀着众差入内坐下,问道:“诸位是那座衙门里来,寻我有何见谕?”王洪道:“小〔的1衙门是甘泉县,因敝上胡太爷有件公事在此,请老爹过目。”说着,在身边取出朱签递过,若愚接过看毕、,大怒道:“这才真真是平地起风波,无影无形的含血喷人。不瞒诸位说,银子有一千两在此,是他无中生有骗信了内子,留他住在舍下,后来因他干出没廉耻的事,无颜对人,又怕我回来见了面更下不去,他即连夜遁走,丢下这宗银子未及取去。我适才正打算退还他,不料他先捏词告我。若说我当面把女儿卖与他作妾,更是笑话,我连认都不认识他。不劳诸位费心,既然我今日回来,无用内子与小女到案,我去当堂与祝自新质个明白,孰是孰非。请诸位少坐,容我进去说知内子等人,即随诸位同行。”张政道:“你老爹做事真称爽快,请到后面吩咐一声,我等在此拱候。”若愚起身入内,对伍氏说,祝自新如何谎告了他。“你们不要害怕,我随差人去审官司,看那小畜生如何说法,真是真假是假,自有公论。快把那一千两银子取出来,我要带了去。”伍氏闻说,很吃了一惊道:“这是那里说起,也亏他忍心撒这样大诳。”兰姑含泪道:“我说姓祝的必要播动是非报复前怨,果不出我所料。只愁他官官相护,父亲须要见机而作为是。”若愚道:“你又多虑了,我本是清白人家,怎能卖起女儿来?难道凭他一面之词,县官即信为实事么?试问我女儿卖与他为妾,有何见证,有何凭据?”兰姑道:“他既饰词谎告,必有一二处使官府相信才可准的状词,父亲不可不防。”若愚点头道:“我都知道,临时自有处置。”伍氏已将银子搬出,若愚取了方布裹好,提在手内,出来同着众差去了。
伍氏关好门户,愈想愈气,顿足大骂道:“祝自新,我把你这天诛地灭,千剐万剁的小畜类,你调戏了人家女儿,反告人昧你银子,不卖女儿与你。只恐你家老婆,日后也要卖与人做小的。”兰姑坐在一旁,不发一言,心如刀割。细想这件事情,“怕的父亲要吃亏苦,一则父亲为人憨直,平空冤枉了他,恐出口即挺撞了县官;二则祝姓既思发手告人,必然安排停当,甚至连身纸等据都可伪造,况他又是个缙绅子弟,难免与县官有旧,若再通了贿赂,分外可虑。”惟有默祷神明保佑他父亲,平安无事回来。又与伍氏商议,央了邻人至县前听信。
不说母女在家愁闷。单说沈若愚到了衙门,张政将他押入班房,派王洪同伙计看管。自己到宅门上来,回说:“被告若愚,今日回家,伍氏母女可不赴案,已将沈若愚带到,请太爷升堂。”宅门进去回明了。少顷,传话二堂伺候。胡武彤入了公座,先唤祝绅家属王德问了一遍,吩咐跪在一旁,方唤沈若愚上来道:“沈若愚,你既将女儿卖与祝乡宦为妾,收过他五百两银子,又立了卖身文约。怎样你妻子伍氏,把祝绅的一千银子骗到了手,陡起图赖的心肠。你想祝家白白丢了一千五百两银子,算是受了你夫妻的骗了,他怎肯干休?如今告到本县衙门,本当办你个通同抵赖,姑念你远在苏州,是你妻子昧良,与你无涉。你好好把女儿送到祝绅家,祝家有了你女儿进门,他断然不记前恨,定要看顾你。你自要明白呀!”沈若愚听罢,叩首道;“真真祝自新冤枉煞小人了,莫说小人家系世代书香,纵然饿死也不肯卖女儿。就连这祝姓,小人都不认识。总怪小人妻子一时胡涂,听信他巧语花言当成真实。他又百般央求,要借住在小人家内,因他夤夜调戏了小人女儿,被小人妻子怒骂一顿,他无颜连夜走了。若说那一千银子,是他住在小人家内,他说外面不便收存,交代小人妻子与他收好。后来他遁去未及携带,丬:非什么身价,他是借此生端的。小人已将银两带来呈堂,请太爷饬祝家收领。至于他所告之词,尽是一派胡言,无半字实情,要求青天太爷做主,先问他个诬栽良民的罪才是。”
胡武彤哈哈大笑道:“沈若愚,本县看你人倒老实,像个忠厚模样,不知道你还讲几句巧话儿搪塞本县,真是人不可貌相。你既说有这一千两银子在你家内,足见祝绅不是冤栽你了。你收过人家银子,又立了文约,想不把女儿交代人家,于理上就说不去。即如将银子退与祝绅,你家妻子无故图赖人银两,又无故的辱骂人,这时候退银子,祝绅都不愿意;你何妨当初不收他银子,如今悔了约,祝绅也无可如何。只怪你做错了,本县是格外加恩,不究前情,你不要自己胡涂,自讨没趣。”
沈若愚听胡武彤句句皆袒护着祝姓,不禁心内火发,那里按耐得住,大声道:“太爷吩咐的话,叫小人死不暝闩。那祝自新有意借端栽害小人,诬良作贱,显而易见。即作他交代小人家银子一千两是有的,小人妻子不合收他银两,不把女儿交出,何以他在苏州只会见小人,又没有见过我女儿何等样人,单凭小人要卖女儿的话,他即兑付五百银子,天下那有这等痴子?再者他的五百银子是由何人交代小人的,不能一千多银子的大事,可以对面讲说的么?就是媒婆,也该要有一名,难不成小人晓得他要买妾,亲自上门去打合他的?况这一张身纸又不是小人笔迹,他既可以诬告,即可假立凭约。此数事彰明较着,要求太爷详察。”一番话,把胡武彤抢白得瞪眼无辞,羞变为怒,将惊堂一拍道:“好大胆忘八蛋,你串同你妻子图赖祝绅银两,昧不交人。本县好意开豁你,只叫你交出女儿,不来办你,还敢强词夺理挺撞本县。先打你个犯上不敬的二十个嘴巴子,再究你昧银匿女的罪。”两旁隶役齐声吆喝,走过三四名粗汉,不由分说把沈若愚拖了下来,如鹰抓燕雀一般,一五一十的掌了二十个嘴巴,打得两腮红肿,口角涔涔流血。沈若愚也不要性命,碰头顿脚的叫起极天冤屈来。胡武彤连连拍案道:“了不得,了不得!你们看这东西可恶不可恶,竟敢在本县堂前肆行无忌。把他押下去,限他三日内交人;这一千银子暂行寄库,俟他交人后仍饬他领了去。”说毕,即起身退堂。原差带了沈若愚下来,交外班房管押。
那听信的邻人如飞回来,对伍氏母女细说堂上如何审问。把伍氏吓得痛哭不已道:“这是那里来的晦气,撞着这瘟官也不问个真伪情由,一味的听信姓祝的话,反打起我家老爹来。我要这条命何用,不如到县前击鼓喊冤,与这瘟官拚了罢!不然我也对不住我家老爹,祸是因我而起的。”兰姑泪纷纷的道:“母亲,你要到县前喊冤,你即喊死了,他也不理。莫若到府里告他一状,告他个问官不明,看他怎样担当得起。”伍氏道:“用得,用得。”忙去央人写了状词,递进府内,又亲到班房里嘱咐若愚,勿用着急,且候府里批示如何,不能府里也像这瘟官胡涂虫。过了一日,府里挂出批来,仍饬甘泉县明白覆讯。
谁知这府官姓毛,即是前任上元县升任到此。刘蕴访得伍氏告了府状,他本与毛知府有交,前次在南京曾托他办过聂家姊妹的。刘蕴与祝自新商议,又备了若干黄白货物,刘蕴亲去拜会,通了贿赂。这毛知府亦是个爱财的人,答应了刘蕴,落得做个好人仍饬甘泉县覆讯,是只受其利,不计其害。胡武彤奉了府文好不得意,又提沈若愚到堂责打,再限三日交人,若仍崛强,定然重究。
伍氏母女得了信,如掉入冷水里相似。实指望府里代他昭雪此案,不料仍发在这瘟官手内,反累了若愚受责。伍氏又要去拚命,兰姑道:“母亲,这不是拚命的事,都要设法救出父亲才是。既然府里不问,难道除了他就没有别的衙门去告状么?我们这地方本系江都县管辖,闻得江都陈太爷是个清正之官,到任以来很干了几桩为民除害兴利的事。因他上省去了,才撞在那瘟官手内。过数日他都要回来的,母亲再去告他一状。若仍是不问,拚着性命去控上状,不怕姓祝的有通天手段,都要拖倒了他。”伍氏称善,只得等江都县回来告状;又愁三日限满;丈夫仍要受责。
恰恰才到两日,打听得江都县今日回衙门。伍氏如半天里得月,忙取了一方乌帕扎在头上,把状词揣在怀内,前去拦舆喊禀,较之投文候批快得多呢!陈小儒轿子将要进衙,伍氏突出叫冤,小儒收了状词,细看情由,不由怒从心起道:“胡礼图太胡闹了,怎样只凭原告一面之词,硬派沈家女儿是卖与他的,也不问个是非曲直。可笑连毛公都胡涂起来,我怕其中定有关节。这沈家本是我该管地方,理宜归我衙门审问。”一面将伍氏暂交官媒看管,一面入衙备了移文,至甘泉县提取原被告人证,及吊核原卷。
胡武彤接着江都移文,大大吃了一惊。知道小儒是个铁面无私的人,非府尊可比,可以颟顸了事。他既回来,被告又在他衙门告发,又是他的汛地,何能不归他承审。倘一经问出祝姓诬告,岂非连我都有处分,左右思维毫无主见,只得把人证原卷先交代了江都来差。自己忙坐轿去会祝自新,叫他赶紧设法料理,不然彼此多有未便。
祝自新前在南京,亦深知小儒利害,急得抓耳挠腮,连呼不妙。刘蕴道:“陈小儒人却古怪,幸喜我与他同年,平日又有一面之交,不若待我去撞个木钟,恳他的情分。但是此人只可以情缚他,却不可以利惑他。一来他是个有家,二来他又是个临财不苟的人。拚我屈了身分去求他,料想他亦不好十分推却。”祝自新听了,连连作揖道:“我真正忘却你与陈公是同年了,即请你去走遭,不可迟缓。虽说是小弟惹下来的祸,也是你仁兄引起头的。”
胡武彤闻刘蕴去见小儒,亦大为喜欢,从旁怂慂道:“难得刘太史与陈公有年谊,只要说得入彀,他纵然开豁了沈若愚,都不致认真追究到祝贤弟身上来。刘太史既与贤弟盟好,断不可坐视不闻。古云:唇亡则齿寒。如说平了此事,连小弟都感激不尽。”你一言我一语逼得刘蕴不容不去,道:“我去是定去,至于行止我却拿不稳,若是别人,不用我去也可成功。”回头叫家丁预备轿子,到县里去拜会。胡武彤又说:“事宜从速,怕的人证到了他衙门,随时即要审问。”仍再三谆嘱了刘蕴几次,方才回衙,还心内悬悬的,候刘蕴回来消息。
少顷,轿子已至,刘蕴穿换公服,带了两名跟随,向江都县来。到了县前,先投了帖进去。小儒正坐在上房与方夫人闲话,说到沈家一案其中定有情弊,好在俟人证提到一讯即知底细。见双福上来回道:“南京刘太史要面会,有要话相商。”小儒看了帖道:“这个宝贝又到扬州来何干?我也无闲会他,你说我沿途受风,不能见客。改日过去谢步,有话再议。”双福去了,少停又上来道:“家人去回复他,他立意要见,硬下了轿坐在花厅上呢。”
小儒无奈,只得出来。刘蕴见面即抢步上前,深躬道:“治生甫至扬州,即闻口碑载道,士庶同称,足见父台恩泽周施。今日探得驺从已回,特专诚晋谒聆教,岂意拒绝太甚,不容一见,想治生多有得罪之处,深为惶恐。”小儒笑道:“仁香兄太谦了,我辈通家年好,言不至此。小弟实因沿途染受些江风:懒于酬对,尚希原谅,容改日登阶谢咎。”刘蕴连称不敢。小儒问道:“年伯老大人足疾可全愈否?”刘蕴欠身答道:“家君足患近日尤甚,医家说是壮年在边省染了山瘴疠气,刻下精力就衰,不能制伏,是以发作起来。纵能调治,都难免偏枯之患。家君仍想医治如恒,进京供职,以残喘报答圣恩。不料心强足违,深以为憾。”又问了问小儒任内的蹊径,遂道:“治生有一事奉乞,都望老父台作成。”即将祝自新告沈家的话,巧言粉饰说了一遍。又道:“敝友祝某非一定要与沈家为难,皆因此事太难为情。他不交出女儿也还罢了,怎样反诬控祝某?况祝某亦系前科副车,是个名教中人,安肯作此违法之事?沈家既不愿女儿与人作妾,祝某亦不能强逼其卖,但要把那以良作贱的事辩明。如沈家认了诬,再将一千五百银子身价退出,祝某即可罢讼。因他是个在案人证,不便干谒。特央治生过来奉求老父台推情,想老父台洞见万里,定不以治生为饰词入告了。”
小儒听刘蕴一派巧言,明知虚浮,“果然祝姓情真理直,又何用托你来致意?”即至听到说祝某系前科副车,忽然触起机来道:“令友祝某莫非即是祝道生么?”刘蕴正说得娓娓入听,不防备小儒问这一句,一时转不过口来,含糊应道:“未知是与不是,治生只知他名自新。”那脸上不禁现出忸怩〔之〕色来,小儒顿时明白,也无须追问,冷笑道:“祝道生我久闻其名,久仰其人,不用仁香兄细嘱,小弟自会关切他,定不负尊托便了。”
说毕,举茶让客,不耐烦与刘蕴多谈,催他起身。刘蕴见话不投机,也难久坐,即作辞出来。回至寓内,祝白新接着,即问道:“其事若何?胡君那边已打发两三起人来问信。”刘蕴因在祝胡二人面前,夸口小儒与他同年至好,一说必从。此时如说出真话来,怕他们要取笑他,只好随口答道:“陈公已应允了,非独重究沈家诬告,还要把他女儿判断与你作妾,叫你不可忘却了他的情分。”祝自新听了,喜得拍手顿足道:“只要他要我为情就好说了,我愿加倍馈送,但求于事有济。”即将刘蕴的话,对胡武彤家人说明,“请你家太爷但放宽心,陈公处刘太史已说通了”。来人去了,祝自新又嘱咐王德,明日赴审小心,须仍照前番说法,不可改变。“你但听陈公口内所问,依着他的口风回就是了”。欢欢喜喜的叫人买了多少酒肴,与刘蕴对饮,专候明日小儒判断。
单说小儒送出刘蕴,回至书房内,暗暗作恼道:“祝道生那畜生,前次在南京与畹秀等作对,把伯青功名都拖累去了。而今-他更名又重新捐纳前程,该应天网恢恢,又至扬州与沈姓争讼,显见他倚势凌压沈家,逼他女儿为妾。不知怎样做成圈套,将一千多银子硬栽在沈家。难得犯在我手内,若审实了他是诬控,必当从重究办,也替伯青报复那一口闷气。”又把原卷取过,细加详阅,心内早有八分了然。
到了次日黎明,升坐大堂,先将原告沈伍氏唤上,问了一遍,吩咐退下。又将沈若愚唤过,细问情由。若愚叩首道:“青天太爷,小人虽习布业,祖父都是学校中人,因小人不肖,未能读书上进克绍箕裘,才改做了买卖。虽然亦是安分清白人家,纵一贫如洗,也不忍把女儿卖人作妾,玷辱家声。何况这祝姓,小人与他向无半面,焉能远在苏州即将女儿出卖,又何以知道他要买妾?他亦安能只凭小人口内之言,即先兑五百两银子?倘若小人没有这个女儿,托言哄骗,他也相信么?再者小人既想赖他银两,何必前日当堂呈缴那一千银子,不如抵赖得毫厘全无,岂不干净?这皆系小人实情,求青天太爷详察。”说毕,连连叩首,小儒亦吩咐他跪在一旁。唤上王德道:“你家主控告沈姓吞银昧女一案,你家主怎样认得沈姓?沈若愚又怎样即将女儿出卖?你须从实细讲,不许半字撒谎。”
王德道:“小的家老主人与沈姓本有交情,并常通往来。后因老主人远出作宦,才算隔绝。日前沈若愚至苏州贩布,在茶坊内偶与家主同桌,谈及上代交谊,甚为相契。家主说因无子要到扬州买妾,问沈若愚久在扬州可知有什么出色的女子。晚间沈若愚即来寻找小的说,闻得你主人要买妾,预备多少身价?小的说只要人品好,我主人合式,一千八百都不吝惜。沈若愚说,我亲生有个女儿,名叫兰姑,今年十七岁,头脸脚手各式皆好。你主人如能出一千五百银子身价,我即定卖与他。但是我与他世交,不好出口,烦你善言为我说成,当重重酬谢,并允定小的事成之日,送小的五十两银子。小的说,你沈老爷的令嫒自然是不得批评的,只恐我主人碍于世交,不敢要你令嫒作妾。沈若愚又再三嘱托了小的数遍,小的即将此言禀知家主。家主始而不行,说我与沈家世交兄弟,何能买他的女儿,要被万人唾骂呢。后来家主被小的劝解说,我看沈老爹目下光景甚窘,亦是出于不得已才肯卖自己女儿。也因我家能出若干银子,又知道驭下宽厚,他女儿可得其所。家主听了小的话,方肯允行。随后沈若愚又亲与家主商量,他东家的本钱被他用空了若干,可能先兑些身价与他弥缝亏空?若恐无凭,我先将卖身纸写送过来,那其余银两,待我女儿过门再行兑付。家主见他说得恳切,又念他是个老实人,故而推诚腹心,先兑了了百银子,沈若愚写下一纸女女儿文契。家主因要先赴扬州,嘱沈若愚写了家信,好至扬州接他女儿,免得日后往返。到了沈家,伍氏看了信亦无异言,当〔即J对家主说,你是我家女婿了,何必住在外面,不如搬至我家来住,也省些客寓用度。二来你即可招赘我家,因我女儿自幼锤爱,我舍不得他远行。今日卖他也是出于无奈,你入赘个十朝半月,让我看看也可放心。家主听他说得有理,即移居他家,择定五日后招亲。次日就将一千两银子,兑交清楚。不料伍氏陡起不良,得了银子,翻转面皮,说家主以良作贱,逼他女儿为妾。伍氏不肯交出女儿,要想悔亲也还罢了,因家主本不愿要他女儿,是受沈若愚蛊惑而成,却不能白白丢了一千多银两,又担个逼良的声名。恰恰沈若愚由苏州回来。家主与他理论,他和伍氏一样的话,足见是预先串合的。家主气极才在县里递禀,沐胡太爷恩断,看破他夫妇伎俩,限三日内交人。伍氏又谎捏情词,在府里与太爷衙门控告。小的所说,句句是实,不敢半字增减。请太爷追究,沈若愚或交原银,或交他女儿,总要有个着落。”小儒点首微笑道:“据你所云,这沈若愚实属可恶,确是个千刁万恶的人,即活活打死,也不足以蔽其辜。但是他写卖身纸的时候,你可亲眼见着没有?”王德道:“沈若愚写契是当着家主与小的面前,亲笔写的,怎么小的没有看见?”小儒道:“既然当着你主仆写的,是他亲笔无疑了。然而本县其中有一处未解,倒要问你。沈若愚兑付五百银子,却写了一千五百银子的契。那一千银子,据你说待他女儿过门方兑,难道沈若愚不怕你主人存了歹念,赖他都付过了?沈若愚应该在契上批注明白,先兑了五百。这是天下人之恒情,他亦五十多岁的人,就该知道这情节,为何他胡里胡涂,就拢统写了?在本县看,沈若愚名虽若愚,恐愚不至此。我疑惑这张契并非是他亲笔所写,乃旁人代他写的,他反受了人家愚弄了。”王德正信口撒谎,讲得活灵活现,不提防小儒在夹缝里问这一句,一时转不过机来,回答不出,急得满脸紫涨,不由口内支吾好半晌,方勉强道:“沈若愚亦因家主是个正经人不须防备,所以才如此写的。好在家主未曾骗他,是他骗家主的。”小儒见王德形色仓惶,心内分外了然,哈哈大笑道:“好个正经人不须防备,你可知沈若愚就吃的这个苦。”顿时反过脸来,把惊堂一拍道:“好大胆奴才,你敢在本县堂前造言生事,帮着你主人害人,你不是助桀为虐么?那沈若愚就与你主人是至亲骨肉,既写到笔据,断无收五百银子肯写一千五百两的文契,天下没有这样痴子。你这该死的奴才,你主仆把沈若愚当做痴子,还来把本县当痴子看待么?代我拖下去结实打。”两边隶役一声吆喝,走过三四个人,把王德揪下。
王德大喊道:“太爷不要打钳了人,没有见过不打骗人的人,反打受骗的人,真正冤枉不浅。”小儒冷笑道:“本县今日偏要错打了你,冤枉了你,拚着你主人去告上状。你须知本县这里,非胡太爷堂上可比,容你胡言乱浯栽害平民。胡太爷是看你的主人情面,本县是玉洁冰清,一尘不染,怎容你这种样子。”说罢,又连声喝“打!”隶役等早将王德拖翻在地,褪下底衣,两个人按住他头脚,一个人举起竹板,用力的朝下打。才打了五板,早巳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因王德自幼跟随尤鼐在任,虽非姣生惯养,亦是享受不尽的人。后来尤鼐卸事,分派伺候仙女婿祝自新,又倚为心腹,除专办外差,平时还有两名三儿服侍。他如何受得起县堂上的刑法,似杀猪一般喊道:“青天太爷,青天菩萨,小的情愿招认了。”小儒止住隶役,放了王德起身,穿好裤子,遂将祝自新与刘蕴如何想谋沈家女儿作妾的话,一一承认。
小儒命招房录了他口供,道:“你主仆做得好圈套,平白地陷害良民,该当何罪?”叫原差带他下去。唤过沈若愚、伍氏道:“你的冤枉,本县已代你问清了,与你夫妇毫无干涉。但是你妻子伍氏,年已半百的人,怎样一点见识没有?皆因妇人家好贪小利,以致丈夫受累。若非本县细心详察,你夫妇真要屈死。以后处世,须要仔细。”。
沈若愚,伍氏朝上连连磕头,如捣蒜相似,齐道:“小人夫妇蒙太爷高厚之恩,雪明冤屈,惟愿太爷高升极品,万代朱衣。”小儒即当堂销案释放,沈家夫妇又叩了几个头,欣然回家去了。到了家中,兰姑见父母双双皆回,急问情由。伍氏将前后的事细说,父女三人甚为感激3当立了长生禄位,朝夕焚香,惟祝恩官早早飞升。
小儒在堂上又点了两名差役,给了堂签,吩咐他到祝自新寓内,提取本人赴案,须要小心。”两名差役退下,即向祝自新寓内来。祝自新因王德去候审,心内悬悬,坐在寓中待信。刘蕴知中有变故,瞒着祝自新悄悄上街去了。两名差役见了祝自新,将堂签收过,假说“本县太爷,现在已审确,沈家昧女吞银是实。他女儿已提到了堂,请你去具结领人”。祝自新听了,喜出望外。刘蕴又不在家,也无人计议,而且昨日说通关节,谅必此事真实不虚,忙换了衣冠,坐轿来至县衙头门外下轿。两名差役领着他上了大堂。
祝自新抬头见小儒坐的是大堂,沈家人影儿都没得半个,又见王德愁眉苦脸的躺在阶下,明知有了变故。又听两名差役唤道:“祝自新带到当面。”祝自新更外着忙,不由心内一阵乱跳,又不能退回,硬着头皮上了堂阶,跪下道:“职员祝自新见父台请安。”小儒淡笑道:“祝道生,你何时更名自新报捐的?”祝自新听得问他的前事,又直呼他的原名道生,早经神不守舍,面上失色道:“职员是祝白新,不是什么祝道生,敢是父台认错了!”小儒道:“本,县前住南京即闻你的大名,如轰雷灌耳,岂有认错之理。本县此时也不及问你更名不更名,朦捐不朦捐。你所控沈家一案,你抱屈家丁王德有一纸口供在此,你且看来。”说着,把王德的供单,掷在祝白新面前。
祝自新拾起看毕,早吓得魂飞云外,魄散风前,暗自恨道:“多怪我用错了王德,这奴才怎么就招认了,岂非要坑杀我?”
再偷觑小儒,见仙端坐堂上,铁铮铮而门,令人害怕。欲待辩白几句,王德已招承了,辩也无益,徒然自取羞辱。只得俯伏在地道:“职员一时胡涂该死,职员知罪了。尚求老父台格外施恩,笔下超生,职员愿甘责罚。”小儒道:“你也知道自己罪名?你还知道你好朋友刘仁香靠不住,他也配向本县讨情么?而且本县两袖清风,既不受人贿嘱。你只好自怨将冰山当做泰山了,你候着详办就是了。”即吩咐两名原差将祝自新领下,交官寓看管王德发外班房监押,“均候本县通详究办”。小儒起身退堂,原差带了祝自新主仆下来。
自新望着王德,顿脚道:“你怎么害了失心疯,把真情都招认了?现在怎么得了。”王德道:“还说了不了,都上了刘蕴那靟养的当。他又未曾说通,我白白地挨了五板,更冤枉呢!我们都不要怨人,只好怨命,该应碰见倒灶鬼。我细想都不派死罪,不过枷打,等我出来了,拚着把刘蕴斲死了,抵他的命。”祝自新亦深为懊悔,痛骂刘蕴。这刘蕴至晚始回寓内,打听得祝家主仆都押起来了。又恐累到自家身上,连夜溜走,也不敢回南京,至别处躲避去了。胡武彤早得了信,急得双脚一阵乱跳道:“完了,完了!我这甘泉县被他们拖掉了,偏偏在收漕的时候,这不是劫数吗!”赶忙坐轿上府,面见毛公,叩求设法。毛公道:“老兄这件事,你也怪不到我。沈伍氏来喊府状,我仍发你衙门审问。你既知道他有胆量告府状,就不怕他去控诉该管的江都县么?即不然,去告了上状,也是累赘。老兄你太任意了,若江都详了上来,我也无力回护。倘或在别人手内还有通融,陈小儒我与他世交至好,他的古怪脾气我巳尽知,他是个反面无情的人。何况目下宪眷甚隆,又保了卓异上去。老兄你不要连我这知府带掉了罢。”胡武彤见毛公都畏惧小儒刚正,格外着急,晓得求他也没用,起身作辞,回来坐在衙门愁闷。
小儒退了堂也不回上房,即下了签押房,连夜叙了通详文书,申详各处。却未提及刘蕴,到底还念同年分上,而且此次他实系因人成事,可以原谅。沈家诉词亦未波及到他身上,便宜了他罢。到了次日,一面详禀各上司衙门,将祝自新更名朦捐,列入首款,使他罪无可逭。又亲自坐轿上府来见毛公,且探一探毛公虚实。遥想此案,他既与刘蕴有旧,刘蕴竟敢来说我入彀,岂有不往说毛公之理。他多该纳贿知情,旁敲侧击他几句,叫他也存个害怕的念头,可以警戒下次。一路上想定主见,已及府衙,投入手版。未知毛公见与不见,见时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