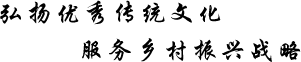第十七回 他考我求他家人代笔
作者:荻岸散人
词曰:
螳螂不量,虾蟆妄想,往往自寻仇。便不伤身,纵能脱祸,也惹一场羞。佳人性慧心肠巧,惯下倒须钩。吞之不入,吐之不出,不怕不低头。
右调《少年游》
话说平如衡考不过侍妾,走了出来。刚走到穿堂背后分路口,撞见燕白颔也走了出来。二人遇见,彼此惊讶。先是燕白颔问道:“你考得如何?”平如衡连连摇头道:“今日出丑了。”燕白颔又问道:“曾见小姐么?”平如衡道:“若见小姐,就考不过还不算出丑。不料小姐自不出来,却叫一个掌书记的侍妾与我同考。那女子虽说是个侍妾,我看他举止端庄,颜色秀媚,比贵家小姐更胜十分。这且勿论,只说那才情敏捷,落笔便成,何须倚马?小弟刚做得一首,他想也不想信笔就和一首。小弟又做了一首,他又信笔和一首。小弟一连做了三首,他略不少停,也一连和了三首。内中情词,针锋相对,不差一线。倒叫小弟不敢再做。我想,一个侍妾,不能讨他半点便宜,岂非出丑。吾兄年遇定不如此,或者为小弟争气?”燕白颔把眉一蹙,道:“不消说起,与兄一样,也是一个书记侍妾,小弟也做了三首,他也和了三首。弄得小弟没法。他见小弟没法,竟笑了进去。临去还题诗一首,讥诮于我。我想,他家侍妾尚然如此高才可爱,那小姐又不知妙到甚么田地!就是小弟所醉心的阁上美人,也不过相为伯仲。小弟所以垂首丧气。不期吾兄也遇劲敌,讨了没趣。”平如衡道:“前边的没趣已过去了,但是出去还要见山相公,倘若问起,何言答之?只怕后面的没趣更觉难当。”燕白颔道:“事既到此,就是难当,也只得当一当。”跟的家人又催。二人立不住脚,只得走了出来。
到了厅上,幸喜得山相公进去,还不曾出来。家人说道:“二位相公请少坐,待我进去,禀知老爷。”燕白颔见山相公不在厅上,巴不得要脱身,因说道:“我们自去,不消禀了。”家人道:“不禀老爷,相公去了,恐怕老爷见罪。”平如衡道:“我们又不是来拜你老爷的,无非是要与小姐试才。今已试过,试的诗又都留在里面,好与歹,听凭你老爷小姐慢慢去看,留我们见老爷做甚么?”家人道:“二位相公既不要见老爷,小的们怎好强留。但只是二位相公尊寓在何处,也须说下,恐怕内里看得诗好,要来相请,也不可知。”平如衡道:“这也说得有理,我二人同寓在……”正要说出玉河桥来,燕白颔慌忙插说道:“同寓在泡子河吕公堂里。”说罢,二人竟往外走。走离了三五十步,燕白颔埋怨平如衡道:“兄好不知机,你看今日这个局面,怎还要对他说出真下处来?”平如衡道:“正是,小弟差了。幸得还未曾说明,亏兄接得好。”
不多时,走到庵前,只见普惠和尚迎着问道:“二位上公怎就出来,莫非不曾见小姐考试么?”燕白颔道:“小姐虽不曾见,考却考过了。”普惠笑道:“相公又来取笑了。小姐若不曾见,谁与相公对考?”平如衡道:“老师不消细问,少不得要知道的。”普惠道:“且请里面吃茶。”二人随了进去。走到佛堂,只见前日题的诗明晃晃写在壁上。二人再自读一遍,觉道词语太狂,因素笔各又续一首于后。燕白颔的道:
青眼从来不浪垂,而今始信有娥眉。
再看脂粉为何物,笔竹千竿墨一池。
平如衡也接过笔来,续一首道:
芳香满耳大名垂,双画千秋才子眉。
人世凤池何足羡,白云西去是瑶池。
普惠在旁看见,因问道:“相公诗中是何意味?小僧全然不识。”燕白颔笑道:“月色溶溶,花阴寂寂,岂容法聪知道。”平如衡又笑道:“他是普惠,又不是普救,怎说这话?”遂相与大笑。别了普惠出来,一径回去不题。
却说山小姐考完,走回后厅,恰好冷绛雪也考完进来。山小姐问道:“那生才学如何?姐姐考得如何?冷绛雪道:“那生是个真正才子,若非贱妾,几乎被他压倒。”因将原韵三首,与自己和韵四首都递与山小姐,道:“小姐请看便知。”山小姐细细看了,喜动眉宇,因说道:“小妹自遭逢圣主垂青,得以诗文遍阅天下才人,于兹五六年也不为少。若不是庸腐之才,就也是疏狂之笔,却从不曾遇此二生,诗才十分俊爽如此。真一时之俊杰也!”冷绛雪道:“这等说来,小姐与考的钱生,想也是个才子了?”山小姐道:“才子不必说,还不是寻常才子,落笔如飞,几令小妹应酬不来。”也将原唱三首并和诗四首递与冷绛雪,道:“姐姐请看过。小妹还有一桩可疑之事与姐姐说。”冷绛雪看了,赞叹不绝,道:“这赵、钱二生,才美真不相上下。不是夸口说,除了小姐与贱妾,却也无人敌得他来。且请问小姐,又有甚可疑之事?”山小姐道:“那生见了小妹‘一曲双成如不如’之句,忽然忘了情,拍案大叫道:“我平如衡今日遇一劲敌矣!”小妹听见,就问他:‘先生姓钱,为何说平如衡?’他着惊,忙忙遮饰。不知为何。莫非此生就是平如衡?不然天下那有许多才子?”冷绛雪道:“那生是怎么样一个人品?”山小姐道:“那生年约二十上下,生得面如瓜子,双眉斜飞入鬓,眼若春星,体度修长,虽弱不胜衣,而神情气宇,昂藏如鹤。”冷绛雪道:“这等说来,正是平如衡了。”只可惜贱妾不曾看见,倒是一番奇遇。”山小姐道:“早知如此,何不姐姐到西园来。”冷绛雪道:“贱妾也有一事可疑。”山小姐道:“何事?”冷绛雪道:“那赵生见贱妾题的‘须知不是并头莲’之句。默然良久,忽叹了一声,低低吟诵道:“天只生人情便了,情长情短有谁怜?”贱妾听了,忙问道:‘此何人所吟?’他答道:‘非吟也,偶有所思耳’。贱妾记得前日小姐和阁下书生正是此二语。莫非这赵生正是阁下书生?”山小姐听了,因问道:“那生生得如何?”冷绛雪道:“那生生得圆面方额,身材清秀而丰满,双肩如两山之耸,一笑如百花之开。古称潘安,虽不知如何之美,只觉此生相近。”山小姐道:“据姐姐想像说来,恍与阁下书生宛然。若果是他,可谓当面错过。”冷绛雪道:“天下事怎这等不凑巧?方才若是小姐在东,贱妾在西,岂不两下对面,真假可以立辨。不意颠颠倒倒,岂非造化弄人?”
二人正踌躇评论,忽山显仁走来,问道:“你二人与两生对考,不知那两生才学实是如何?”山小姐答道:“那两生俱天下奇才,父亲须优礼相待才是。”山显仁道:“我正出去留他,不知他为甚竟不别而去。我故进来问你。既果是真才,还须着人赶转,问他个详细才是。”山小姐道:“父亲所言最是。”
山显仁遂走了出来,叫一个家人到接引庵去问:“若是赵、钱二相公还在庵中,定然要请转来。若是去了,就问普惠,临去可曾有甚话说。”家人领命到庵中去问。普惠回说道:“已去久了。临去并无话说,只在前题壁诗后又题了二首而去。”家人遂将二诗抄了,来回复山显仁。山显仁看了,因自来与女儿并冷绛雪看,道:“我只恐他匆匆而去,有甚不足之处,今见二诗,十分钦羡于你。不别而去者,大约是怀惭之意了。”山小姐道:“此二生不独才高,而又虚心服善如此,真难得!”冷绛雪道:“难得两个都是一般高才。”山显仁见女儿与冷绛雪交口称赞,因又吩咐一个家人道:“方才来考试的松江赵、钱二位相公,寓在城中泡子河吕公堂,你可拿我两个名帖去请他,有话说。”
家人领命,到次日起个早,果走到泡子河吕公堂来寻问。燕白颔原是假说,如何寻问得着。不其事有凑巧,宋信因张尚书府中出入不便,故借寓在此。山府家人左问右问,竟问到宋信下处。宋信见了,问道:“你是谁家来的?寻那一个?”家人答道:“我是山府来的,要寻松江赵、钱二位相公。”宋信道:“山府自然是山相公了。”家人道:“正是,现有名帖在此。”宋信看见上面写着“侍生山显仁拜”,因又问道:“这赵、钱二相公与你老爷有甚相知,却来请他?”家人道:“这二位相公昨日在我府与小姐对考,老爷与小姐见他是两个才子,故此请他去,有甚话说。”宋信心下暗想道:“此二人一定是考中意的了。此二人若考中了意,老张的事情便无望了。”因打个破头屑道:“松江只有张吏部老爷的公子张寅便是个真才子,哪里有甚姓赵姓钱的才子!莫非被人骗了?”家人道:“昨日明明两个青年相公在我府中考试的,怎么是骗了?”宋信道:“若不是骗,就是你错记了姓名?”家人道:“明明一个姓赵,一个姓钱,为何会错?”宋信道:“松江城中的朋友,我都相交尽了,且莫说才子,就是饱学秀才也没个姓赵姓钱的,莫非还是张寅相公?”家人道:“不曾说姓张。”宋信道:“若不是姓张,这里没有。”家人只得又到各处去寻。寻了一日,并无踪影。”只得回复山显仁道:“小人到吕公堂遍访,并无二人踪迹。人人说松江才子只有张吏部老爷的公子张寅才是,除他并无别个。”山显仁道:“胡说!明明两人在此,你们都是见的,怎么没有?定是不用心访。还不快去细访,若再访不着便要重责!”家人慌了,只得又央了两个,同进城去访不题。
却说宋信得了这个消息,忙寻见张寅,将前事说了一遍,道:“这事不上心,只管弄冷了。”张寅道:“不是我不上心,他哪里又定要见我?你又叫我不要去,所以耽延。为今之计,将如之何?”宋信道:“他既看中意了赵钱二人,今虽寻不见,终须寻着。一寻见了,便有成机,便将我们前功尽弃。如今急了,俗语说得好:‘丑媳妇少不得要见公婆。’真若讨两封硬挣书,大着胆,乘他寻不见二人之际,去走一道。倘侥幸先下手成了,也不可知。若是要考试诗文,待小弟躲在外边,代作一两首,传递与兄,塞塞白儿,包你妥帖。只是事成了,不要忘却小弟。”张寅道:“兄如此玉成,自当重报。”
二人算计停当,果然又讨了两封要路的书,先送了去。随即自写了名帖,又备了一副厚礼,自家阔服乘轿来拜。又将宋信悄悄藏在左近人家。山显仁看了书帖,皆都是称赞张寅少年才美、门当户对,求亲之意。又见书帖都是一时权贵;又因是吏部尚书之子;又见许多礼物,不好轻慢,只得叫人请入相见。
张寅倚着自家有势,竟昂然走到厅上,以晚辈礼相见。礼毕,看坐在左首,山显仁下陪。一面奉茶,一面山显仁就问道:“久仰贤契青年高才,渴欲一会,怎么许久不蒙下顾?”张寅答道:“晚生一到京,老父即欲命晚生趋谒老太师,不意途中劳顿,抱恙未痊,所以羁迟上谒,获罪不胜。”山显仁道:“原来有恙。老夫急于领教,也无他事。因见前日书中盛称贤契著述甚富,故欲领教一二。”张寅道:“晚生未学,巴人下里之词,只好涂饰闾里,怎敢陈于老太师山斗之下。今既蒙诱引,敢不献丑。”因向跟的家人取了《张子新编》一册,深深打一恭,送上道:“鄙陋之章,敢求老太师转致令爱小姐笔削。”山显仁接了,展开一看,见《迁柳庄》、《题壁》、《听莺》诸作字字清新,十分欢喜,道:“贤契美才,可谓名下无虚。”又看了两首,津津有味。因叫家人送与小姐,一面就邀张寅到后厅留饮。张寅辞逊不得,只得随到后厅。
小饮数杯,山显仁又问道:“云间大郡,人文之邦。前日王督学特荐一个燕白颔,也是松江人,贤契可是相知么?”张寅道:“这燕白颔号紫侯,也是敝县华亭人,与晚生是自幼同窗,最为莫逆。凡遇考事,第一第二,每每与晚生不相上下。才是有些,只是为人狂妄,出语往往诋毁前辈,乡里以此薄之。家父常说他,既承宗师荐举,又蒙圣奋发征召,就不该不俟驾而来。却又不知向何方流荡,竟无踪迹,以辜朝廷德意。岂是上进之人?”山显仁听了,道:“原来这燕生如此薄劣!纵使有才,亦不足重。”
正说未完,只见一个家人走在山显仁耳边,低低说些甚么。山显仁就说道:“小女见了佳章,十分欣羡。因内中有甚未解处,要请贤契到玉尺楼一解。不识贤契允否?”张寅道:“晚生此来正要求教小姐。得蒙赐问,是所愿也。”山显仁道:“既是这等,可请一往,老夫在此奉候。”就叫几个家人送到玉尺楼去。张寅临行,山显仁又说道:“小女赋性端严,又不能容物,比不得老夫,贤契言语须要谨慎。”张寅打一恭道:“谨领台命。”遂跟了家人同往,心下暗想道:“山老之言过于自大,他阁老女儿纵然贵重,我尚书之子也不寒贱,难道敢轻薄我不成?怕他怎的!若要十分小心,倒转被他看轻了。”主意定了,遂昂昂然随着家人入去。 不期这玉尺楼直在花园后边,走过了许多亭榭曲廊,方才到了楼下。家人请他坐下,叫侍妾传话上楼。坐不多时,只见楼上走下两侍妾来,向张寅说道:“小姐请问张相公,这《张子新编》还是自作的,不是选集众人的?”张寅见问得突然,不觉当心一拳,急得面皮通红,幸喜得小姐不在面前,只得勉强硬说道:“上面明明刻着《张子新编》,张子就是我张相公了,怎说是别人做的?”侍妾道:“小姐说,既是张相公自做的,为何连平如衡的诗都刻在上面?”张寅听见说出“平如衡”三字,摸着根脚,惊得哑口无言。默然半晌,只得转口说道:“你家小姐果然有眼力,果然是个才子。后面有两首是平如衡与我唱和做的,故此连他的都刻在上面。”侍妾道:“小姐说:‘不独平如衡两首,还有别人的哩。’”张寅心下暗想道:“他既然看出平如衡的来,自然连燕白颔都知道,莫若直认了罢。”因说道:“除了平如衡,便是燕白颔还有两首,其余是我的了,再无别人。请小姐只管细看。我张相公是真才实学,决不做那盗袭小人之事。”
侍妾上楼复命。不多时,又走下楼来,手里拿着一幅字,递与张寅,道:“小姐说《张子新编》既是张相公自做的,定然是一个奇才子,今题诗一首在此,求张相公和韵。”张寅接了,打开一看,只见上写着一首绝句,道:
一池野草不成莲,满树杨花岂是绵?
失去燕平旧时句,忽然张子有《新编》。
张寅见了,一时没摆布,只得假推要和,磨墨拈笔,写来写去。悄悄写了一个稿儿,趁人眼不见,递与贴身一个童子,叫他传出去,与宋信代做。自家口里哼哼唧唧的沉吟。一会儿虚写了两句,一会儿又抹去了两句,一会儿又将原稿读两遍,一会儿又起身走两步,两只眼只望着外边。侍儿们看了,俱微微含笑。挨的工夫久了,楼上又走下两上侍妾来。催促道:“小姐问张相公,方才这首诗还是和,还是不知?”张寅道:“怎么不和?”侍儿道:“既然和,为何只管做去?”张寅道:“诗妙于工,潦草不得。况诗人之才情不同:李太白斗酒百篇,杜工部吟诗太瘦,如何一样论得?”正然着急不题。
却说小童拿了一张诗稿,忙忙走出,要寻宋信代作。奈房子深远,转折甚多,一时认不得出路,只在东西乱撞。不期冷绛雪听得山小姐在玉尺楼考张寅,要走去看看。正走出房门,忽撞见小童乱走,因叫侍妾捉住,问道:“你是甚么人,走到内里来?”小童慌了,说道:“我是跟张相公的。”冷绛雪道:“你跟张相公,为何在此乱走?”小童道:“我要出去,因认不得路错走在此。”冷绛雪见他说话慌张,定有缘故,因说道:“你既跟张相公,又出去做甚?定是要做贼了,快拿到老爷处去问。”小童慌了,道:“实是相公吩咐出去有事,并不是做贼。”冷绛雪道:“你实说出去做甚么,我就饶你。你若说一句谎,我就拿你去。”小童要脱身又脱不得,只得实说道:“相公要做甚么诗,叫我传出去,与宋相公代做。”冷绛雪道:“要做甚么诗,可拿与我看。”小童没法,只得取出来递与冷绛雪。冷绛雪看了,笑一笑道:“这是小姐奈何他了。待我也取笑他一场。”因对小童说道:“你不消出去寻人,等我替你做了罢。”小童道:“若是小姐肯做得,一发好了。”冷绛雪道:“跟我来。”遂带了小童到房中,信笔写了两首,递与他道:“你可拿去,只说是宋相公做的。”小童得了诗,欢喜不过。冷绛雪又叫侍儿送他到楼下。 小童掩将进去,张寅忽然看见,慌忙推小解,走到阶下。那童子近身一混,就将代做的诗递了过来。张寅接诗在手,便胆大气壮,昂昂然走进来坐下道:“凡做诗要有感触,偶下阶有触,不觉诗便成了。”因暗暗将代做的稿儿铺在纸下。原打帐是一首,见是两首,一发快活,因照样誊写。写完,又自念一遍,十分得意。因递与侍妾道:“诗已和成,可拿与小姐去细看。小姐乃有才之人,自识其中趣味。”
侍妾接了,微笑一笑,遂走上楼来与山小姐。山小姐接了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
高才自负落花莲,莫认包儿掉了绵。
纵是燕平旧时句,云间张子实重编。
又一首是:
荷花荷叶总成莲,树长蚕生都是绵。
莫道《春秋》齐晋事,一加笔削仲尼编。
山小姐看完,不禁大笑道:“这个白丁,不知央甚人代作,倒被他取笑了!”又看一遍道:“诗虽游戏,其实风雅,则代作者倒是一个才子。但不知是何人?怎做个法儿,叫他说出万妙。”
正然沉吟,忽冷绛雪从后楼转了出来。山小姐忙迎着笑,说道:“姐姐来得好!又有一个才子,可看一个笑话。”冷绛雪笑道:“这个笑话,我已看见;这个才子,我已先知。”山小姐道:“姐姐才来,为何倒先知道了?”冷绛雪就将撞见小童出去求人代作,并自己代他作诗之事说了一遍。山小姐拍掌大笑,道:“原来就是姐姐耍他!我说哪里又有一个才子?”
张寅在楼下听见楼上笑声哑哑,满心认为看诗欢喜,因暗想道:“何不乘他欢喜,赶上楼去调戏,得个趣儿。倘有天缘,彼此爱慕,固是万幸;就是他心下不允,我是一个尚书公子,又是他父亲明明叫我进来的,他也不好难为我。今日若当面错过,明日再央人来求,不知费许多力气,还是隔靴搔痒,不能如此亲切。”主意定了,遂不顾好歹,竟硬着胆撞上楼来。只因这一上楼来,有分教:黄金上公子之头,红粉涂才郎之面。不知此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螳螂不量,虾蟆妄想,往往自寻仇。便不伤身,纵能脱祸,也惹一场羞。佳人性慧心肠巧,惯下倒须钩。吞之不入,吐之不出,不怕不低头。
右调《少年游》
话说平如衡考不过侍妾,走了出来。刚走到穿堂背后分路口,撞见燕白颔也走了出来。二人遇见,彼此惊讶。先是燕白颔问道:“你考得如何?”平如衡连连摇头道:“今日出丑了。”燕白颔又问道:“曾见小姐么?”平如衡道:“若见小姐,就考不过还不算出丑。不料小姐自不出来,却叫一个掌书记的侍妾与我同考。那女子虽说是个侍妾,我看他举止端庄,颜色秀媚,比贵家小姐更胜十分。这且勿论,只说那才情敏捷,落笔便成,何须倚马?小弟刚做得一首,他想也不想信笔就和一首。小弟又做了一首,他又信笔和一首。小弟一连做了三首,他略不少停,也一连和了三首。内中情词,针锋相对,不差一线。倒叫小弟不敢再做。我想,一个侍妾,不能讨他半点便宜,岂非出丑。吾兄年遇定不如此,或者为小弟争气?”燕白颔把眉一蹙,道:“不消说起,与兄一样,也是一个书记侍妾,小弟也做了三首,他也和了三首。弄得小弟没法。他见小弟没法,竟笑了进去。临去还题诗一首,讥诮于我。我想,他家侍妾尚然如此高才可爱,那小姐又不知妙到甚么田地!就是小弟所醉心的阁上美人,也不过相为伯仲。小弟所以垂首丧气。不期吾兄也遇劲敌,讨了没趣。”平如衡道:“前边的没趣已过去了,但是出去还要见山相公,倘若问起,何言答之?只怕后面的没趣更觉难当。”燕白颔道:“事既到此,就是难当,也只得当一当。”跟的家人又催。二人立不住脚,只得走了出来。
到了厅上,幸喜得山相公进去,还不曾出来。家人说道:“二位相公请少坐,待我进去,禀知老爷。”燕白颔见山相公不在厅上,巴不得要脱身,因说道:“我们自去,不消禀了。”家人道:“不禀老爷,相公去了,恐怕老爷见罪。”平如衡道:“我们又不是来拜你老爷的,无非是要与小姐试才。今已试过,试的诗又都留在里面,好与歹,听凭你老爷小姐慢慢去看,留我们见老爷做甚么?”家人道:“二位相公既不要见老爷,小的们怎好强留。但只是二位相公尊寓在何处,也须说下,恐怕内里看得诗好,要来相请,也不可知。”平如衡道:“这也说得有理,我二人同寓在……”正要说出玉河桥来,燕白颔慌忙插说道:“同寓在泡子河吕公堂里。”说罢,二人竟往外走。走离了三五十步,燕白颔埋怨平如衡道:“兄好不知机,你看今日这个局面,怎还要对他说出真下处来?”平如衡道:“正是,小弟差了。幸得还未曾说明,亏兄接得好。”
不多时,走到庵前,只见普惠和尚迎着问道:“二位上公怎就出来,莫非不曾见小姐考试么?”燕白颔道:“小姐虽不曾见,考却考过了。”普惠笑道:“相公又来取笑了。小姐若不曾见,谁与相公对考?”平如衡道:“老师不消细问,少不得要知道的。”普惠道:“且请里面吃茶。”二人随了进去。走到佛堂,只见前日题的诗明晃晃写在壁上。二人再自读一遍,觉道词语太狂,因素笔各又续一首于后。燕白颔的道:
青眼从来不浪垂,而今始信有娥眉。
再看脂粉为何物,笔竹千竿墨一池。
平如衡也接过笔来,续一首道:
芳香满耳大名垂,双画千秋才子眉。
人世凤池何足羡,白云西去是瑶池。
普惠在旁看见,因问道:“相公诗中是何意味?小僧全然不识。”燕白颔笑道:“月色溶溶,花阴寂寂,岂容法聪知道。”平如衡又笑道:“他是普惠,又不是普救,怎说这话?”遂相与大笑。别了普惠出来,一径回去不题。
却说山小姐考完,走回后厅,恰好冷绛雪也考完进来。山小姐问道:“那生才学如何?姐姐考得如何?冷绛雪道:“那生是个真正才子,若非贱妾,几乎被他压倒。”因将原韵三首,与自己和韵四首都递与山小姐,道:“小姐请看便知。”山小姐细细看了,喜动眉宇,因说道:“小妹自遭逢圣主垂青,得以诗文遍阅天下才人,于兹五六年也不为少。若不是庸腐之才,就也是疏狂之笔,却从不曾遇此二生,诗才十分俊爽如此。真一时之俊杰也!”冷绛雪道:“这等说来,小姐与考的钱生,想也是个才子了?”山小姐道:“才子不必说,还不是寻常才子,落笔如飞,几令小妹应酬不来。”也将原唱三首并和诗四首递与冷绛雪,道:“姐姐请看过。小妹还有一桩可疑之事与姐姐说。”冷绛雪看了,赞叹不绝,道:“这赵、钱二生,才美真不相上下。不是夸口说,除了小姐与贱妾,却也无人敌得他来。且请问小姐,又有甚可疑之事?”山小姐道:“那生见了小妹‘一曲双成如不如’之句,忽然忘了情,拍案大叫道:“我平如衡今日遇一劲敌矣!”小妹听见,就问他:‘先生姓钱,为何说平如衡?’他着惊,忙忙遮饰。不知为何。莫非此生就是平如衡?不然天下那有许多才子?”冷绛雪道:“那生是怎么样一个人品?”山小姐道:“那生年约二十上下,生得面如瓜子,双眉斜飞入鬓,眼若春星,体度修长,虽弱不胜衣,而神情气宇,昂藏如鹤。”冷绛雪道:“这等说来,正是平如衡了。”只可惜贱妾不曾看见,倒是一番奇遇。”山小姐道:“早知如此,何不姐姐到西园来。”冷绛雪道:“贱妾也有一事可疑。”山小姐道:“何事?”冷绛雪道:“那赵生见贱妾题的‘须知不是并头莲’之句。默然良久,忽叹了一声,低低吟诵道:“天只生人情便了,情长情短有谁怜?”贱妾听了,忙问道:‘此何人所吟?’他答道:‘非吟也,偶有所思耳’。贱妾记得前日小姐和阁下书生正是此二语。莫非这赵生正是阁下书生?”山小姐听了,因问道:“那生生得如何?”冷绛雪道:“那生生得圆面方额,身材清秀而丰满,双肩如两山之耸,一笑如百花之开。古称潘安,虽不知如何之美,只觉此生相近。”山小姐道:“据姐姐想像说来,恍与阁下书生宛然。若果是他,可谓当面错过。”冷绛雪道:“天下事怎这等不凑巧?方才若是小姐在东,贱妾在西,岂不两下对面,真假可以立辨。不意颠颠倒倒,岂非造化弄人?”
二人正踌躇评论,忽山显仁走来,问道:“你二人与两生对考,不知那两生才学实是如何?”山小姐答道:“那两生俱天下奇才,父亲须优礼相待才是。”山显仁道:“我正出去留他,不知他为甚竟不别而去。我故进来问你。既果是真才,还须着人赶转,问他个详细才是。”山小姐道:“父亲所言最是。”
山显仁遂走了出来,叫一个家人到接引庵去问:“若是赵、钱二相公还在庵中,定然要请转来。若是去了,就问普惠,临去可曾有甚话说。”家人领命到庵中去问。普惠回说道:“已去久了。临去并无话说,只在前题壁诗后又题了二首而去。”家人遂将二诗抄了,来回复山显仁。山显仁看了,因自来与女儿并冷绛雪看,道:“我只恐他匆匆而去,有甚不足之处,今见二诗,十分钦羡于你。不别而去者,大约是怀惭之意了。”山小姐道:“此二生不独才高,而又虚心服善如此,真难得!”冷绛雪道:“难得两个都是一般高才。”山显仁见女儿与冷绛雪交口称赞,因又吩咐一个家人道:“方才来考试的松江赵、钱二位相公,寓在城中泡子河吕公堂,你可拿我两个名帖去请他,有话说。”
家人领命,到次日起个早,果走到泡子河吕公堂来寻问。燕白颔原是假说,如何寻问得着。不其事有凑巧,宋信因张尚书府中出入不便,故借寓在此。山府家人左问右问,竟问到宋信下处。宋信见了,问道:“你是谁家来的?寻那一个?”家人答道:“我是山府来的,要寻松江赵、钱二位相公。”宋信道:“山府自然是山相公了。”家人道:“正是,现有名帖在此。”宋信看见上面写着“侍生山显仁拜”,因又问道:“这赵、钱二相公与你老爷有甚相知,却来请他?”家人道:“这二位相公昨日在我府与小姐对考,老爷与小姐见他是两个才子,故此请他去,有甚话说。”宋信心下暗想道:“此二人一定是考中意的了。此二人若考中了意,老张的事情便无望了。”因打个破头屑道:“松江只有张吏部老爷的公子张寅便是个真才子,哪里有甚姓赵姓钱的才子!莫非被人骗了?”家人道:“昨日明明两个青年相公在我府中考试的,怎么是骗了?”宋信道:“若不是骗,就是你错记了姓名?”家人道:“明明一个姓赵,一个姓钱,为何会错?”宋信道:“松江城中的朋友,我都相交尽了,且莫说才子,就是饱学秀才也没个姓赵姓钱的,莫非还是张寅相公?”家人道:“不曾说姓张。”宋信道:“若不是姓张,这里没有。”家人只得又到各处去寻。寻了一日,并无踪影。”只得回复山显仁道:“小人到吕公堂遍访,并无二人踪迹。人人说松江才子只有张吏部老爷的公子张寅才是,除他并无别个。”山显仁道:“胡说!明明两人在此,你们都是见的,怎么没有?定是不用心访。还不快去细访,若再访不着便要重责!”家人慌了,只得又央了两个,同进城去访不题。
却说宋信得了这个消息,忙寻见张寅,将前事说了一遍,道:“这事不上心,只管弄冷了。”张寅道:“不是我不上心,他哪里又定要见我?你又叫我不要去,所以耽延。为今之计,将如之何?”宋信道:“他既看中意了赵钱二人,今虽寻不见,终须寻着。一寻见了,便有成机,便将我们前功尽弃。如今急了,俗语说得好:‘丑媳妇少不得要见公婆。’真若讨两封硬挣书,大着胆,乘他寻不见二人之际,去走一道。倘侥幸先下手成了,也不可知。若是要考试诗文,待小弟躲在外边,代作一两首,传递与兄,塞塞白儿,包你妥帖。只是事成了,不要忘却小弟。”张寅道:“兄如此玉成,自当重报。”
二人算计停当,果然又讨了两封要路的书,先送了去。随即自写了名帖,又备了一副厚礼,自家阔服乘轿来拜。又将宋信悄悄藏在左近人家。山显仁看了书帖,皆都是称赞张寅少年才美、门当户对,求亲之意。又见书帖都是一时权贵;又因是吏部尚书之子;又见许多礼物,不好轻慢,只得叫人请入相见。
张寅倚着自家有势,竟昂然走到厅上,以晚辈礼相见。礼毕,看坐在左首,山显仁下陪。一面奉茶,一面山显仁就问道:“久仰贤契青年高才,渴欲一会,怎么许久不蒙下顾?”张寅答道:“晚生一到京,老父即欲命晚生趋谒老太师,不意途中劳顿,抱恙未痊,所以羁迟上谒,获罪不胜。”山显仁道:“原来有恙。老夫急于领教,也无他事。因见前日书中盛称贤契著述甚富,故欲领教一二。”张寅道:“晚生未学,巴人下里之词,只好涂饰闾里,怎敢陈于老太师山斗之下。今既蒙诱引,敢不献丑。”因向跟的家人取了《张子新编》一册,深深打一恭,送上道:“鄙陋之章,敢求老太师转致令爱小姐笔削。”山显仁接了,展开一看,见《迁柳庄》、《题壁》、《听莺》诸作字字清新,十分欢喜,道:“贤契美才,可谓名下无虚。”又看了两首,津津有味。因叫家人送与小姐,一面就邀张寅到后厅留饮。张寅辞逊不得,只得随到后厅。
小饮数杯,山显仁又问道:“云间大郡,人文之邦。前日王督学特荐一个燕白颔,也是松江人,贤契可是相知么?”张寅道:“这燕白颔号紫侯,也是敝县华亭人,与晚生是自幼同窗,最为莫逆。凡遇考事,第一第二,每每与晚生不相上下。才是有些,只是为人狂妄,出语往往诋毁前辈,乡里以此薄之。家父常说他,既承宗师荐举,又蒙圣奋发征召,就不该不俟驾而来。却又不知向何方流荡,竟无踪迹,以辜朝廷德意。岂是上进之人?”山显仁听了,道:“原来这燕生如此薄劣!纵使有才,亦不足重。”
正说未完,只见一个家人走在山显仁耳边,低低说些甚么。山显仁就说道:“小女见了佳章,十分欣羡。因内中有甚未解处,要请贤契到玉尺楼一解。不识贤契允否?”张寅道:“晚生此来正要求教小姐。得蒙赐问,是所愿也。”山显仁道:“既是这等,可请一往,老夫在此奉候。”就叫几个家人送到玉尺楼去。张寅临行,山显仁又说道:“小女赋性端严,又不能容物,比不得老夫,贤契言语须要谨慎。”张寅打一恭道:“谨领台命。”遂跟了家人同往,心下暗想道:“山老之言过于自大,他阁老女儿纵然贵重,我尚书之子也不寒贱,难道敢轻薄我不成?怕他怎的!若要十分小心,倒转被他看轻了。”主意定了,遂昂昂然随着家人入去。 不期这玉尺楼直在花园后边,走过了许多亭榭曲廊,方才到了楼下。家人请他坐下,叫侍妾传话上楼。坐不多时,只见楼上走下两侍妾来,向张寅说道:“小姐请问张相公,这《张子新编》还是自作的,不是选集众人的?”张寅见问得突然,不觉当心一拳,急得面皮通红,幸喜得小姐不在面前,只得勉强硬说道:“上面明明刻着《张子新编》,张子就是我张相公了,怎说是别人做的?”侍妾道:“小姐说,既是张相公自做的,为何连平如衡的诗都刻在上面?”张寅听见说出“平如衡”三字,摸着根脚,惊得哑口无言。默然半晌,只得转口说道:“你家小姐果然有眼力,果然是个才子。后面有两首是平如衡与我唱和做的,故此连他的都刻在上面。”侍妾道:“小姐说:‘不独平如衡两首,还有别人的哩。’”张寅心下暗想道:“他既然看出平如衡的来,自然连燕白颔都知道,莫若直认了罢。”因说道:“除了平如衡,便是燕白颔还有两首,其余是我的了,再无别人。请小姐只管细看。我张相公是真才实学,决不做那盗袭小人之事。”
侍妾上楼复命。不多时,又走下楼来,手里拿着一幅字,递与张寅,道:“小姐说《张子新编》既是张相公自做的,定然是一个奇才子,今题诗一首在此,求张相公和韵。”张寅接了,打开一看,只见上写着一首绝句,道:
一池野草不成莲,满树杨花岂是绵?
失去燕平旧时句,忽然张子有《新编》。
张寅见了,一时没摆布,只得假推要和,磨墨拈笔,写来写去。悄悄写了一个稿儿,趁人眼不见,递与贴身一个童子,叫他传出去,与宋信代做。自家口里哼哼唧唧的沉吟。一会儿虚写了两句,一会儿又抹去了两句,一会儿又将原稿读两遍,一会儿又起身走两步,两只眼只望着外边。侍儿们看了,俱微微含笑。挨的工夫久了,楼上又走下两上侍妾来。催促道:“小姐问张相公,方才这首诗还是和,还是不知?”张寅道:“怎么不和?”侍儿道:“既然和,为何只管做去?”张寅道:“诗妙于工,潦草不得。况诗人之才情不同:李太白斗酒百篇,杜工部吟诗太瘦,如何一样论得?”正然着急不题。
却说小童拿了一张诗稿,忙忙走出,要寻宋信代作。奈房子深远,转折甚多,一时认不得出路,只在东西乱撞。不期冷绛雪听得山小姐在玉尺楼考张寅,要走去看看。正走出房门,忽撞见小童乱走,因叫侍妾捉住,问道:“你是甚么人,走到内里来?”小童慌了,说道:“我是跟张相公的。”冷绛雪道:“你跟张相公,为何在此乱走?”小童道:“我要出去,因认不得路错走在此。”冷绛雪见他说话慌张,定有缘故,因说道:“你既跟张相公,又出去做甚?定是要做贼了,快拿到老爷处去问。”小童慌了,道:“实是相公吩咐出去有事,并不是做贼。”冷绛雪道:“你实说出去做甚么,我就饶你。你若说一句谎,我就拿你去。”小童要脱身又脱不得,只得实说道:“相公要做甚么诗,叫我传出去,与宋相公代做。”冷绛雪道:“要做甚么诗,可拿与我看。”小童没法,只得取出来递与冷绛雪。冷绛雪看了,笑一笑道:“这是小姐奈何他了。待我也取笑他一场。”因对小童说道:“你不消出去寻人,等我替你做了罢。”小童道:“若是小姐肯做得,一发好了。”冷绛雪道:“跟我来。”遂带了小童到房中,信笔写了两首,递与他道:“你可拿去,只说是宋相公做的。”小童得了诗,欢喜不过。冷绛雪又叫侍儿送他到楼下。 小童掩将进去,张寅忽然看见,慌忙推小解,走到阶下。那童子近身一混,就将代做的诗递了过来。张寅接诗在手,便胆大气壮,昂昂然走进来坐下道:“凡做诗要有感触,偶下阶有触,不觉诗便成了。”因暗暗将代做的稿儿铺在纸下。原打帐是一首,见是两首,一发快活,因照样誊写。写完,又自念一遍,十分得意。因递与侍妾道:“诗已和成,可拿与小姐去细看。小姐乃有才之人,自识其中趣味。”
侍妾接了,微笑一笑,遂走上楼来与山小姐。山小姐接了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
高才自负落花莲,莫认包儿掉了绵。
纵是燕平旧时句,云间张子实重编。
又一首是:
荷花荷叶总成莲,树长蚕生都是绵。
莫道《春秋》齐晋事,一加笔削仲尼编。
山小姐看完,不禁大笑道:“这个白丁,不知央甚人代作,倒被他取笑了!”又看一遍道:“诗虽游戏,其实风雅,则代作者倒是一个才子。但不知是何人?怎做个法儿,叫他说出万妙。”
正然沉吟,忽冷绛雪从后楼转了出来。山小姐忙迎着笑,说道:“姐姐来得好!又有一个才子,可看一个笑话。”冷绛雪笑道:“这个笑话,我已看见;这个才子,我已先知。”山小姐道:“姐姐才来,为何倒先知道了?”冷绛雪就将撞见小童出去求人代作,并自己代他作诗之事说了一遍。山小姐拍掌大笑,道:“原来就是姐姐耍他!我说哪里又有一个才子?”
张寅在楼下听见楼上笑声哑哑,满心认为看诗欢喜,因暗想道:“何不乘他欢喜,赶上楼去调戏,得个趣儿。倘有天缘,彼此爱慕,固是万幸;就是他心下不允,我是一个尚书公子,又是他父亲明明叫我进来的,他也不好难为我。今日若当面错过,明日再央人来求,不知费许多力气,还是隔靴搔痒,不能如此亲切。”主意定了,遂不顾好歹,竟硬着胆撞上楼来。只因这一上楼来,有分教:黄金上公子之头,红粉涂才郎之面。不知此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