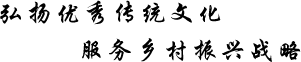第八十一回
作者:徐哲身
第八十一回悲月影空房来怪妇奋神威废院歼花妖话说蔡谙等正苦没有住处,林英用手向前面一指,说道:“看那树林里面,不是有灯光闪出吗?显见是有人家的去处啊!”蔡谙和胡明齐朝前面一望,只见前面的树林里,果然有一丝灯光,从树林中直透出来。蔡谙大喜,忙对二人说道:“惭愧,今天不是那里有人家,险些儿要没处息宿哩!”林英道:“可不是么?我们就去罢!”
说话时,三人马上加鞭,三匹马穿云价地直向那灯光的去处而来。一转树林,果然露出一座小小的村落来。三人在黑暗里,还能辨认一些,只见檐牙屋角,参差错落,只能望见大概,可是夜深了,一切都沉寂了,静悄悄地连鸡犬都不闻。三人下了马,各自牵着缰绳,走到第一家门口,向门里一瞧。只见里面黑黝黝的一点灯光也没有。胡明便要上前敲门。蔡谙忙道:“胡将军休要乱动!这里人家大约已是睡熟了,我们到别家去借宿罢!”胡明听他这话,忙住了手。又走第二家,仍然是双扉紧闭,一些声息也没有。林英啧啧地奇怪道:“我们方才不是看见这里有灯光的么?怎的走到这里,反而不见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蔡谙笑道:“这一点道理你都不明白。我们在远处看来,这里差不多全在眼中。现在到了跟前,只能一家一家的在我们的眼中,那有灯光的人家,或许在后面,也未可知。
再则这有灯光的人家,现在已经睡了,亦未可知。“林英点首称是。三人顺着这个村落,一直向西寻去,刚走村落的中间,瞥见有个黑影子,蹲在墙根旁边。把个蔡谙吓得倒退几步,林英忙问道:”什么缘故?“蔡谙附着他耳朵,悄悄地说道:”看那墙根下面黑黪黪的是个什么东西?你去看看!“林英拔出佩剑,走到前面,故意咳嗽一声。只见那黑影子忽然立了起来,大声问道:”半夜三更的,你是什么人,在这里转什么念头?“林英才知道他是个人,忙走近来低声说道:“请问这里可有宿店没有?”那人说道:“有的,有的,你们几个人?”林英忙答道:“三个。”那人道:“你走这里一直朝西去,前边就是宿店了。”
说话时,靠身边一家人家,忽地将门开了,里面露出灯光来,照在那人的脸上,只见他已经须眉魔白了。从里面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人来,将老头子搀扶着说道:“老爷子,你老人家这几天肚子里不适意,应该请郎中先生来诊视诊视才好呢。
夜里常常到外面解手,万一受了风,可不是耍的。”那老头子跷起胡子说道:“不打紧,不打紧,用不着你们来担心。”
他们说着,走进门去,砰然一声,将门关起。
蔡谙等忙向西而来,走了数家,果然见一家门口悬着一个幌子,门内灯光还未熄去,门边还有一块招牌,上面有几个字,因为天时黑暗,辨不出是什么字来。胡明性急,便大踏步走上前,用手在门上砰砰砰敲得震天价响的。里面有人问道:“谁敲门呀?”胡明答道:“我们是下店的,烦你开一开门罢!”
那里的人答道:“下店在酉牌以前,现在不下了。”胡明道:“请你开门罢,因为我们远途而来,一时寻不到下宿的地方,所以到这会才到这里的。”里面答道:“不行,不行。我们这里没有这种规矩的,你们到别处去罢!”胡明按不住心头火起,大声说道:“你这里的人,好不讲道理,咱们下店,又不是不给钱的,为什么偏要推东阻西的?难道你们的招牌上标明过了酉时就不下客么?”蔡谙忙道:“胡将军!他不下就罢了,何苦与他去口辩作什么来。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自古道,东村不下客,西有一千家呢!”
说话时,门已开了,走出一个身高九尺的大汉来。上面穿一件蓝布短袄,露着一只碗粗的赤膊在外面,下面围着一条虎皮的腰裙,双目陷入印堂,高鼻阔口,满面横肉,打量他这个样子,竟像一个屠户。只听得他扬声问道:“哪里来的几个鸟人,在这里吵闹什么?咱家不下客,难道你一定要强迫我们下客不成?”
胡明把那一股无明的业火,高举三千丈,按捺不下,抢过来,劈面就是一拳,那大汉原是个惯家,忙将身子一侧,让过一拳。胡明一拳,没有打中,身子往前一倾,忙立定脚,正要再来第二拳,哪知那大汉趁势一掌,向胡明太阳穴打来。胡明晓得厉害,赶紧将头一偏。谁知大汉早已将掌收回,冷不提防他一腿,从下面扫来。
胡明手灵眼快双脚一纵,又让过了他一腿。正要还手,瞥见那大汉狂吼一声,扑地倒下。不能动弹了。胡明莫名其妙,立在一旁,直是朝那大汉发呆。这时林英走到那大汉跟前,喝道:“好杂种!你想欺负我们远来的旅客么?今朝可先给你一个厉害。”那大汉血流满面,躺在地下,只是哀告道:“爷爷们,请高抬贵手!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万望饶命。”林英冷笑一声说道:“你可知道咱们的厉害了。”
那大汉只是央求饶命。林英才俯下身子,将他一把拉起来,用手朝他的右眼一点。那大汉怪叫一声,身子一矮,右眼中吐出一颗弹子来。林英喝道:“快点去将上好的房间收拾出来,让咱们住!”这时店里的小伙子、走堂的一齐拥了出来,预备帮着大汉动手。瞥见那大汉走了下风,谁敢还来讨死呢?齐声附和道:“就去办,就去办。”胡明还要去动手,蔡谙一把扯住道:“彀了,彀了,让人一着不为痴。”这时那小厮吓得手忙脚乱,牵马的牵马,备饭的备饭,鸟乱得一天星斗。蔡谙倒老大不忍。一会子盥面漱口,接着吃了晚饭。胡明问道:“哪里是我们的住宿地方?”那此小厮,没口地答应道:“有,有,有,请客官们随我们进来吧!”
蔡谙随着那个秃头小厮,直向后面,一连进了几重房子,到了最后面一宅房子,一共是三间,靠着一所废院,门朝南。
他们进了门,仔细一看,原来是两暗一明。里面每间里设着一张杨木榻帐子被褥,倒也洁净,一切用具都是灰尘满布,好像许久没有住过人的样子。蔡谙不禁疑惑起来,忙向那秃头小厮问道:“你们这里,别处可有房间么?”那小厮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地说道:“今天的生意,真是好极了,别处一间空房也没有了。”蔡谙又问道:“我看这房间里,好像许多天没有住过的样子。”那秃头小厮答道:“果然,果然。因为我们这里平常没有什么客人来下店,所以这房子只好空起在这里预备着,如果客人多了就将此地卖钱了。”胡明忙道:“那么,这里既然空着三个房间,方才那个汉子,为何又说不下客呢?”
秃头小厮答道:“客官们不知道,原来有个缘故。”蔡谙忙问那小厮道:“什么缘故呢?”秃头小厮突然噎住了,翻着双眼只是发呆。
林英倒疑惑起来,大声喝道:“小狗头,又要捣什么鬼?
有什么话,赶紧好好的从实说来,不要怄得咱老子性起,一把将你这小狗头摔得稀烂。“那秃头小厮,吓得屁滚尿流,忙跪下来央求道:”爷爷息怒,小的就说。
“蔡谙忙叫他立起来。
那小厮立起来。吞吞吐吐地说道:“我们这里有个例子,到了酉牌一过,就不下客了,别的没有什么缘故。”林英道:“叵耐这小杂种捣鬼,说来说去,不过这两句话,给我滚出去。”
那个秃头小厮,得到了这一句,宛如逢着救星一般,一溜烟地出去了。
蔡谙对林、胡二将说道:“请各自去安息罢,明天还要赶路呢!”林英正色对蔡谙说道:“我看这店里的人,鬼头鬼脑的倒不可不防备一些呢!”蔡谙说道:“可不是么?出门的人,都以小心一点为是,不要大意才好呢!”胡明大笑道:“你们也忒过虑了,眼见那个牛子已经吃足了苦头,还敢再来捋虎须么?我不相信。”
材英道:“这倒不要大意,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胡明哪里在心,笑嘻嘻地走进房间去睡觉。林英也到西边一个房间里去了。
蔡谙在中间明间里,他一个人坐在床前,思前想后,又不知何日方可到天竺,将经取了,了却大愿。寻思一阵,烦上心来,哪里还睡得着,背着手在屋于里踱来踱去,踱了半天。这时候只有两边房间里的鼾声,和外边的秋虫唧唧的声音,互相酬答着,破这死僵的空气,其余也没有第三种声音来混杂的。
蔡谙闷得好不耐烦,便开了门,朝外面一望,只见星移斗换,一轮明月,已从东边升起。这时正当深秋的时候,凉飙吹来,将那院里的树木吹得簌簌地作响。他信步走出门来,对着月亮,仰面看了好久,才又将头低下,心中暗暗地触动了无限闲愁,思妻想子,十分难过,信步走到一座破坏的茅亭里,坐了一会。
那些秋虫似乎知道他的心思,兀地哽哽咽咽叫个不住,反觉增加了他的悲伤,暗自叹道:“悔不该当初承认这件事的,如今受尽千般辛苦,万种凄凉,还不知何时才到天竺灵山呢?沿途能安安稳稳的,将经求回,就不负我一番苦心了;万一发生了什么乱子,那就不堪设想了。”他自言自语地一会子,猛地起了一阵怪风,吹得他毛发直竖,坐不住,便立起来要走。
这时星月陡然没有什么光彩了,周近的树木,只是簌簌地作响。蔡谙此时心中害怕起来,便大三步小两步地跑进门来,将门关好,挑去烛花,又坐了一会,觉得渐渐地困倦起来,便懒洋洋地走到自己的床前,面朝外往下一坐,用手将头巾除下,放在桌上;又将长衣脱下,回过身来,正要放下,瞥见一个国色无双的佳人,坐在他的身子后面。他可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忙要下床,无奈两条腿好像被什么东西绊着的一样,再也抬不起头来。又要开口喊人,可是再也喊不出来。真个是心头撞小鹿,面上泛红光,瞪着两只眼睛,朝着那女子只是发呆。只见她梳着堕马髻,上身穿着一件湖绉小袄,下身系着宫妆百褶裙,一双金莲瘦尖尖的不满三寸,桃腮梨面,星眼樱唇,端的是倾国倾城,天然姿色。
蔡谙定了一定神,仗着胆问道:“你这位姑娘,半夜三更,到我的床上做甚?男女授受不亲,赶紧回去,不要胡思乱想!
须知我蔡谙一不是贪花浪子,二不是好色登徒。人生在世,名节为重,不要以一念之差,致贻羞于万世。“他说了这几句,满想将这女子劝走。谁知她不独纹丝不动,反而轻抒皓腕,伸出一双纤纤玉手,将蔡谙的手轻轻握祝吓得蔡谙躲避不迭的,已经被她握住了,觉得软滑如脂,不禁心中一跳,忙按住心神。
只听她轻启朱唇,悄悄地向他笑道:“谁来寻你的?这里本是我的住处,今天被你占了,你反说我来寻你的,真是岂有此理!”蔡谙忙道:“既是小姐的卧榻,蔡某何人,焉敢强占呢?请放手,让我到他们那里息宿罢!”那女子哪里肯放手让他走,一双玉手,紧紧地握住,斜瞟星眼,向他一笑,然后娇声说道:“不要做作罢,到哪里去息宿去?今天难得天缘巧遇,就此。”她说到这里,嫣然向他一笑。
这一笑,真是百媚俱生,任你是个无情的铁汉,也要道我见犹怜,谁能遣此哩!蔡谙定了定心神,正色地向她说道:“小姐千万不要如此,为人不要贪图片刻欢乐,损失终身的名誉。”她微露瓢犀说道:“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要知奴家亦非人尽可夫之辈,今天见君丰姿英爽,遂料定是一位大英雄,大豪杰,不料果然中了奴家估量。良宵甚短,佳期不常,请勿推辞罢!”蔡谙此时正是弄得进退两难:想要脱身,无奈被她紧紧地握住双手。想要声张,又恐大家知道了难以见人。只怕得浑身发软,满面绯红。
她见他这样,不禁嗤的一声,悄悄地笑道:“君家真是一个未见世面的拙男子了,见了这样的美色当前,还不知道消受,莫非你怕羞么?你我二人在此地,要做什么,便做什么,怕谁来呢?”她说罢,扭股糖似地搂着蔡谙,将粉腮偎到他的脸上,轻轻亲了一个嘴。把个蔡谙弄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是躲让不祝她笑道:“请你不要尽来做作了,快点宽衣解带,同上巫山吧!”蔡谙此时被她缠得神魂不定,鼻子里一阵一阵地触着粉香脂气,一颗心不禁突突地跳了起来,满面发烧,那一般孽火从小肚子下面直泛到丹田上面,暗道:“不好,不好,今天可要耐不住了。”
想着,赶紧按定了心神,寻思了一阵子,猛地想起:“这女子来时,不是没有看见吗?而且我亲眼看见那秃头小厮收拾床铺的。怎的我出去一会子,她就来了,莫非是鬼么?”他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忽然又转过念头,自己对自己说道:“不是,不是。如果她是鬼,就不会开口说话了。”他定睛朝这女子的粉面上细细地打量了一会子,却也未曾看出什么破绽来,那一张吹弹得破的粉庞上面,除却满藏春色,别的一点看不出什么的色彩来。蔡谙暗想道:“无论她是人是鬼,能够在半夜淫奔,可见不是好货。”他想到这里,将那一片羞愧的心,转化了憎恶,不禁厉声喊道:“林将军!”
他一声还未喊完,只见她死力用手将他的嘴掩住,一手便来硬扯他的下衣。蔡谙死力拽着。正在这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林英正自睡得正浓,猛听得蔡谙喊了一声。他原是个极其精细的人,便从梦中惊醒,霍了坐了起来,侧耳细听,不见得有什么动静,他不禁倒疑惑起来,暗道:“我方才不是清清楚楚地听见得蔡中郎的声音么,怎的现在又不听见动静呢?敢是我疑心罢了。”他想到这里,便又复行睡下。猛可里听得蔡谙喘喘吁吁的声音说道:“无论如何,要想我和你做那些可耻的事情,那是做不到的。”林英听得,大吃一惊,忙又坐起,取了宝剑,轻手轻脚地下了床,蹑足潜踪地走取房门口,探头朝外面一望,只见明间里的蜡烛还未熄去;又见蔡谙的帐子,乱搔乱动,似乎有人在里面做什么勾当似的。林英一脚纵到蔡谙的床前,伸手将帐子一揭,定睛一看,瞥见一个绝色的女子,搂着蔡谙,正在那里纠缠不休。
林英按不住心头火起。蔡谙见了林英前来,便仗了胆,喊道:“林将军!快来救我一救!”林英剔起眼睛,大声喝道:“好不要脸的东西,还不放下手,再迟一会,休怪咱老子剑下无情。”
谁知那女子娇嗔满面,一撒手好似穿花粉蝶一般地飞下床来,向林英喝道:“我和他作耍与你何干?谁教你这匹夫来破坏我们的好事?须知娘也不是好惹的。”她说话时,便在腰间掣出两口双峰剑来,圆睁杏眼向林英喝道:“好匹夫,快来送死罢!”林英更是怒不可遏,挥剑就砍,她举剑相迎大战了三十多合,未见胜负。
这时屋里面只听得叮叮噹的宝剑声音,把个蔡谙吓得抖做一团,无地可入。这时林英一面敌住那女子,又恐怕她去害蔡谙;一面又到蔡谙床前,展开兵刃掩护着。又战了五十多合,林英越战越勇,杀得那女子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能,香汗盈盈,娇喘细细。林英挥着宝剑,一步紧一步地逼祝那女子杀到分际,虚晃一刃,跳出圈子,开门就走。
林英哪里肯舍,一纵身赶了出来。二人又在天井里搭了手,乒乒乓乓地大杀起来。再说胡明睡到半夜的时候,被尿涨得醒了。一时又寻不着尿壶,赤身露体地奔了出来,正要撒尿。猛地听得厮杀声音,吃惊不小,忙定睛一看,只见林英和一个女子,正在那里舍死忘生地恶斗,他可着了急,连尿也不撒了,跑到自己的房里,将一对卧爪大锤取了出来,赤着身子,跑了出来,大吼一声,耍动双锤助战那女子。
那女子正被林英杀得招架不来,还能再加上一个吗?只往后退,一直退到一棵老树的旁边,被胡明觑准一锤。只听得壳秃一声,那女子早巳不知去向,将那棵老树砍了倒下。这正是:妖姬甘作先生妾,宝剑能枭荡妇头。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doubleads();
说话时,三人马上加鞭,三匹马穿云价地直向那灯光的去处而来。一转树林,果然露出一座小小的村落来。三人在黑暗里,还能辨认一些,只见檐牙屋角,参差错落,只能望见大概,可是夜深了,一切都沉寂了,静悄悄地连鸡犬都不闻。三人下了马,各自牵着缰绳,走到第一家门口,向门里一瞧。只见里面黑黝黝的一点灯光也没有。胡明便要上前敲门。蔡谙忙道:“胡将军休要乱动!这里人家大约已是睡熟了,我们到别家去借宿罢!”胡明听他这话,忙住了手。又走第二家,仍然是双扉紧闭,一些声息也没有。林英啧啧地奇怪道:“我们方才不是看见这里有灯光的么?怎的走到这里,反而不见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蔡谙笑道:“这一点道理你都不明白。我们在远处看来,这里差不多全在眼中。现在到了跟前,只能一家一家的在我们的眼中,那有灯光的人家,或许在后面,也未可知。
再则这有灯光的人家,现在已经睡了,亦未可知。“林英点首称是。三人顺着这个村落,一直向西寻去,刚走村落的中间,瞥见有个黑影子,蹲在墙根旁边。把个蔡谙吓得倒退几步,林英忙问道:”什么缘故?“蔡谙附着他耳朵,悄悄地说道:”看那墙根下面黑黪黪的是个什么东西?你去看看!“林英拔出佩剑,走到前面,故意咳嗽一声。只见那黑影子忽然立了起来,大声问道:”半夜三更的,你是什么人,在这里转什么念头?“林英才知道他是个人,忙走近来低声说道:“请问这里可有宿店没有?”那人说道:“有的,有的,你们几个人?”林英忙答道:“三个。”那人道:“你走这里一直朝西去,前边就是宿店了。”
说话时,靠身边一家人家,忽地将门开了,里面露出灯光来,照在那人的脸上,只见他已经须眉魔白了。从里面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人来,将老头子搀扶着说道:“老爷子,你老人家这几天肚子里不适意,应该请郎中先生来诊视诊视才好呢。
夜里常常到外面解手,万一受了风,可不是耍的。”那老头子跷起胡子说道:“不打紧,不打紧,用不着你们来担心。”
他们说着,走进门去,砰然一声,将门关起。
蔡谙等忙向西而来,走了数家,果然见一家门口悬着一个幌子,门内灯光还未熄去,门边还有一块招牌,上面有几个字,因为天时黑暗,辨不出是什么字来。胡明性急,便大踏步走上前,用手在门上砰砰砰敲得震天价响的。里面有人问道:“谁敲门呀?”胡明答道:“我们是下店的,烦你开一开门罢!”
那里的人答道:“下店在酉牌以前,现在不下了。”胡明道:“请你开门罢,因为我们远途而来,一时寻不到下宿的地方,所以到这会才到这里的。”里面答道:“不行,不行。我们这里没有这种规矩的,你们到别处去罢!”胡明按不住心头火起,大声说道:“你这里的人,好不讲道理,咱们下店,又不是不给钱的,为什么偏要推东阻西的?难道你们的招牌上标明过了酉时就不下客么?”蔡谙忙道:“胡将军!他不下就罢了,何苦与他去口辩作什么来。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自古道,东村不下客,西有一千家呢!”
说话时,门已开了,走出一个身高九尺的大汉来。上面穿一件蓝布短袄,露着一只碗粗的赤膊在外面,下面围着一条虎皮的腰裙,双目陷入印堂,高鼻阔口,满面横肉,打量他这个样子,竟像一个屠户。只听得他扬声问道:“哪里来的几个鸟人,在这里吵闹什么?咱家不下客,难道你一定要强迫我们下客不成?”
胡明把那一股无明的业火,高举三千丈,按捺不下,抢过来,劈面就是一拳,那大汉原是个惯家,忙将身子一侧,让过一拳。胡明一拳,没有打中,身子往前一倾,忙立定脚,正要再来第二拳,哪知那大汉趁势一掌,向胡明太阳穴打来。胡明晓得厉害,赶紧将头一偏。谁知大汉早已将掌收回,冷不提防他一腿,从下面扫来。
胡明手灵眼快双脚一纵,又让过了他一腿。正要还手,瞥见那大汉狂吼一声,扑地倒下。不能动弹了。胡明莫名其妙,立在一旁,直是朝那大汉发呆。这时林英走到那大汉跟前,喝道:“好杂种!你想欺负我们远来的旅客么?今朝可先给你一个厉害。”那大汉血流满面,躺在地下,只是哀告道:“爷爷们,请高抬贵手!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万望饶命。”林英冷笑一声说道:“你可知道咱们的厉害了。”
那大汉只是央求饶命。林英才俯下身子,将他一把拉起来,用手朝他的右眼一点。那大汉怪叫一声,身子一矮,右眼中吐出一颗弹子来。林英喝道:“快点去将上好的房间收拾出来,让咱们住!”这时店里的小伙子、走堂的一齐拥了出来,预备帮着大汉动手。瞥见那大汉走了下风,谁敢还来讨死呢?齐声附和道:“就去办,就去办。”胡明还要去动手,蔡谙一把扯住道:“彀了,彀了,让人一着不为痴。”这时那小厮吓得手忙脚乱,牵马的牵马,备饭的备饭,鸟乱得一天星斗。蔡谙倒老大不忍。一会子盥面漱口,接着吃了晚饭。胡明问道:“哪里是我们的住宿地方?”那此小厮,没口地答应道:“有,有,有,请客官们随我们进来吧!”
蔡谙随着那个秃头小厮,直向后面,一连进了几重房子,到了最后面一宅房子,一共是三间,靠着一所废院,门朝南。
他们进了门,仔细一看,原来是两暗一明。里面每间里设着一张杨木榻帐子被褥,倒也洁净,一切用具都是灰尘满布,好像许久没有住过人的样子。蔡谙不禁疑惑起来,忙向那秃头小厮问道:“你们这里,别处可有房间么?”那小厮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地说道:“今天的生意,真是好极了,别处一间空房也没有了。”蔡谙又问道:“我看这房间里,好像许多天没有住过的样子。”那秃头小厮答道:“果然,果然。因为我们这里平常没有什么客人来下店,所以这房子只好空起在这里预备着,如果客人多了就将此地卖钱了。”胡明忙道:“那么,这里既然空着三个房间,方才那个汉子,为何又说不下客呢?”
秃头小厮答道:“客官们不知道,原来有个缘故。”蔡谙忙问那小厮道:“什么缘故呢?”秃头小厮突然噎住了,翻着双眼只是发呆。
林英倒疑惑起来,大声喝道:“小狗头,又要捣什么鬼?
有什么话,赶紧好好的从实说来,不要怄得咱老子性起,一把将你这小狗头摔得稀烂。“那秃头小厮,吓得屁滚尿流,忙跪下来央求道:”爷爷息怒,小的就说。
“蔡谙忙叫他立起来。
那小厮立起来。吞吞吐吐地说道:“我们这里有个例子,到了酉牌一过,就不下客了,别的没有什么缘故。”林英道:“叵耐这小杂种捣鬼,说来说去,不过这两句话,给我滚出去。”
那个秃头小厮,得到了这一句,宛如逢着救星一般,一溜烟地出去了。
蔡谙对林、胡二将说道:“请各自去安息罢,明天还要赶路呢!”林英正色对蔡谙说道:“我看这店里的人,鬼头鬼脑的倒不可不防备一些呢!”蔡谙说道:“可不是么?出门的人,都以小心一点为是,不要大意才好呢!”胡明大笑道:“你们也忒过虑了,眼见那个牛子已经吃足了苦头,还敢再来捋虎须么?我不相信。”
材英道:“这倒不要大意,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胡明哪里在心,笑嘻嘻地走进房间去睡觉。林英也到西边一个房间里去了。
蔡谙在中间明间里,他一个人坐在床前,思前想后,又不知何日方可到天竺,将经取了,了却大愿。寻思一阵,烦上心来,哪里还睡得着,背着手在屋于里踱来踱去,踱了半天。这时候只有两边房间里的鼾声,和外边的秋虫唧唧的声音,互相酬答着,破这死僵的空气,其余也没有第三种声音来混杂的。
蔡谙闷得好不耐烦,便开了门,朝外面一望,只见星移斗换,一轮明月,已从东边升起。这时正当深秋的时候,凉飙吹来,将那院里的树木吹得簌簌地作响。他信步走出门来,对着月亮,仰面看了好久,才又将头低下,心中暗暗地触动了无限闲愁,思妻想子,十分难过,信步走到一座破坏的茅亭里,坐了一会。
那些秋虫似乎知道他的心思,兀地哽哽咽咽叫个不住,反觉增加了他的悲伤,暗自叹道:“悔不该当初承认这件事的,如今受尽千般辛苦,万种凄凉,还不知何时才到天竺灵山呢?沿途能安安稳稳的,将经求回,就不负我一番苦心了;万一发生了什么乱子,那就不堪设想了。”他自言自语地一会子,猛地起了一阵怪风,吹得他毛发直竖,坐不住,便立起来要走。
这时星月陡然没有什么光彩了,周近的树木,只是簌簌地作响。蔡谙此时心中害怕起来,便大三步小两步地跑进门来,将门关好,挑去烛花,又坐了一会,觉得渐渐地困倦起来,便懒洋洋地走到自己的床前,面朝外往下一坐,用手将头巾除下,放在桌上;又将长衣脱下,回过身来,正要放下,瞥见一个国色无双的佳人,坐在他的身子后面。他可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忙要下床,无奈两条腿好像被什么东西绊着的一样,再也抬不起头来。又要开口喊人,可是再也喊不出来。真个是心头撞小鹿,面上泛红光,瞪着两只眼睛,朝着那女子只是发呆。只见她梳着堕马髻,上身穿着一件湖绉小袄,下身系着宫妆百褶裙,一双金莲瘦尖尖的不满三寸,桃腮梨面,星眼樱唇,端的是倾国倾城,天然姿色。
蔡谙定了一定神,仗着胆问道:“你这位姑娘,半夜三更,到我的床上做甚?男女授受不亲,赶紧回去,不要胡思乱想!
须知我蔡谙一不是贪花浪子,二不是好色登徒。人生在世,名节为重,不要以一念之差,致贻羞于万世。“他说了这几句,满想将这女子劝走。谁知她不独纹丝不动,反而轻抒皓腕,伸出一双纤纤玉手,将蔡谙的手轻轻握祝吓得蔡谙躲避不迭的,已经被她握住了,觉得软滑如脂,不禁心中一跳,忙按住心神。
只听她轻启朱唇,悄悄地向他笑道:“谁来寻你的?这里本是我的住处,今天被你占了,你反说我来寻你的,真是岂有此理!”蔡谙忙道:“既是小姐的卧榻,蔡某何人,焉敢强占呢?请放手,让我到他们那里息宿罢!”那女子哪里肯放手让他走,一双玉手,紧紧地握住,斜瞟星眼,向他一笑,然后娇声说道:“不要做作罢,到哪里去息宿去?今天难得天缘巧遇,就此。”她说到这里,嫣然向他一笑。
这一笑,真是百媚俱生,任你是个无情的铁汉,也要道我见犹怜,谁能遣此哩!蔡谙定了定心神,正色地向她说道:“小姐千万不要如此,为人不要贪图片刻欢乐,损失终身的名誉。”她微露瓢犀说道:“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要知奴家亦非人尽可夫之辈,今天见君丰姿英爽,遂料定是一位大英雄,大豪杰,不料果然中了奴家估量。良宵甚短,佳期不常,请勿推辞罢!”蔡谙此时正是弄得进退两难:想要脱身,无奈被她紧紧地握住双手。想要声张,又恐大家知道了难以见人。只怕得浑身发软,满面绯红。
她见他这样,不禁嗤的一声,悄悄地笑道:“君家真是一个未见世面的拙男子了,见了这样的美色当前,还不知道消受,莫非你怕羞么?你我二人在此地,要做什么,便做什么,怕谁来呢?”她说罢,扭股糖似地搂着蔡谙,将粉腮偎到他的脸上,轻轻亲了一个嘴。把个蔡谙弄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是躲让不祝她笑道:“请你不要尽来做作了,快点宽衣解带,同上巫山吧!”蔡谙此时被她缠得神魂不定,鼻子里一阵一阵地触着粉香脂气,一颗心不禁突突地跳了起来,满面发烧,那一般孽火从小肚子下面直泛到丹田上面,暗道:“不好,不好,今天可要耐不住了。”
想着,赶紧按定了心神,寻思了一阵子,猛地想起:“这女子来时,不是没有看见吗?而且我亲眼看见那秃头小厮收拾床铺的。怎的我出去一会子,她就来了,莫非是鬼么?”他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忽然又转过念头,自己对自己说道:“不是,不是。如果她是鬼,就不会开口说话了。”他定睛朝这女子的粉面上细细地打量了一会子,却也未曾看出什么破绽来,那一张吹弹得破的粉庞上面,除却满藏春色,别的一点看不出什么的色彩来。蔡谙暗想道:“无论她是人是鬼,能够在半夜淫奔,可见不是好货。”他想到这里,将那一片羞愧的心,转化了憎恶,不禁厉声喊道:“林将军!”
他一声还未喊完,只见她死力用手将他的嘴掩住,一手便来硬扯他的下衣。蔡谙死力拽着。正在这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林英正自睡得正浓,猛听得蔡谙喊了一声。他原是个极其精细的人,便从梦中惊醒,霍了坐了起来,侧耳细听,不见得有什么动静,他不禁倒疑惑起来,暗道:“我方才不是清清楚楚地听见得蔡中郎的声音么,怎的现在又不听见动静呢?敢是我疑心罢了。”他想到这里,便又复行睡下。猛可里听得蔡谙喘喘吁吁的声音说道:“无论如何,要想我和你做那些可耻的事情,那是做不到的。”林英听得,大吃一惊,忙又坐起,取了宝剑,轻手轻脚地下了床,蹑足潜踪地走取房门口,探头朝外面一望,只见明间里的蜡烛还未熄去;又见蔡谙的帐子,乱搔乱动,似乎有人在里面做什么勾当似的。林英一脚纵到蔡谙的床前,伸手将帐子一揭,定睛一看,瞥见一个绝色的女子,搂着蔡谙,正在那里纠缠不休。
林英按不住心头火起。蔡谙见了林英前来,便仗了胆,喊道:“林将军!快来救我一救!”林英剔起眼睛,大声喝道:“好不要脸的东西,还不放下手,再迟一会,休怪咱老子剑下无情。”
谁知那女子娇嗔满面,一撒手好似穿花粉蝶一般地飞下床来,向林英喝道:“我和他作耍与你何干?谁教你这匹夫来破坏我们的好事?须知娘也不是好惹的。”她说话时,便在腰间掣出两口双峰剑来,圆睁杏眼向林英喝道:“好匹夫,快来送死罢!”林英更是怒不可遏,挥剑就砍,她举剑相迎大战了三十多合,未见胜负。
这时屋里面只听得叮叮噹的宝剑声音,把个蔡谙吓得抖做一团,无地可入。这时林英一面敌住那女子,又恐怕她去害蔡谙;一面又到蔡谙床前,展开兵刃掩护着。又战了五十多合,林英越战越勇,杀得那女子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能,香汗盈盈,娇喘细细。林英挥着宝剑,一步紧一步地逼祝那女子杀到分际,虚晃一刃,跳出圈子,开门就走。
林英哪里肯舍,一纵身赶了出来。二人又在天井里搭了手,乒乒乓乓地大杀起来。再说胡明睡到半夜的时候,被尿涨得醒了。一时又寻不着尿壶,赤身露体地奔了出来,正要撒尿。猛地听得厮杀声音,吃惊不小,忙定睛一看,只见林英和一个女子,正在那里舍死忘生地恶斗,他可着了急,连尿也不撒了,跑到自己的房里,将一对卧爪大锤取了出来,赤着身子,跑了出来,大吼一声,耍动双锤助战那女子。
那女子正被林英杀得招架不来,还能再加上一个吗?只往后退,一直退到一棵老树的旁边,被胡明觑准一锤。只听得壳秃一声,那女子早巳不知去向,将那棵老树砍了倒下。这正是:妖姬甘作先生妾,宝剑能枭荡妇头。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double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