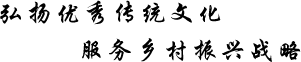第四十一回
作者:李逸侯
第四十一回曹后怜才免兴冤狱神宗尽孝谨守遗言神宗至是也大不满意王安石了,遂准他解职,命以使相出判江宁府,不久,改为集禧观使。王安石出居金陵后,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福建子是指吕惠卿,因为是深悔被吕惠卿所误,这且不提。王安石既去,神宗乃擢吴充、王珪同平章事,冯京知枢密院事,蔡确参知政事。吴充与王安石为儿女亲家,吴充素不赞成王安石所为,每向神宗奏陈新法不良,神宗至是喜他不党附王安石,擢为宰相。冯京与王安石乃是同年,王安石致吕惠卿私书中“勿令齐年知”一语,就是指冯京,所以神宗此时便认冯京为贤者,召他知枢密院事。
吴充意想将新法变革一二,自顾才学谫陋,乃奏请神宗召还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又举荐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神宗乃召吕公著同知枢密院事,进程颢判武学。程颢自扶沟县入京,任职才数日,李定、何正臣便劾他学术迂阔,趋向僻易,神宗仍命他还任原官去了。吕公著上疏谏阻,竟不得请。司马光在洛听得吴充颇有更正弊政的心志,乃致书吴充,陈述救济时弊的方法。司马光书云:自新法之行,中外汹汹,民困于烦苛,迫于诛敛,愁怨流离,转死沟壑,日夜引领,冀朝廷觉悟,一变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当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谋。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开言路以悟人主之心。
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为痼疾矣。吴充得书,颇想照司马光的意见,请神宗罢除“青苗”、“免役”、“保甲、”
市易“诸新法,广开言路以征求多士意见。蔡确听得,暗吃一惊,若是罢免了这些新法,引进忠良,他便要像化子没了蛇弄,不能再有饱饭吃,忙向吴充道:”这些新法怎能变更得呢?皇上费了多少勤劳,才得到今日的成绩,我辈好意思请求他废掉吗?而今只有萧规曹随,遵守前制,才是继往开来的善策。若一更变,便惹万代骂名了!“吴充听了,惧怕起来,不敢采用司马光的建议,仍旧履行新法。因此,王安石虽然罢了相位,新法却是一点也没有变更什么。
忽一日,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劾奏知湖州苏轼,怨望朝廷,毁谤君父,交通戚里,诚属大不敬,请严格究治。神宗大怒,降诏逮苏轼入都,下付台狱。原来苏轼前因论新法不便,谪贬杭州后,再徙于徐州,不久又徙湖州。他一路游山玩水,放情诗酒,消磨他郁郁不得志的烦恼岁月,也尝借着吟咏讥讽朝政。摘句如次:咏青苗云: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咏水利云: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课吏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咏盐禁云: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像这一类的诗歌,不胜枚举,原不过诗人一时感触,发为吟咏,并不是真个存着什么大不敬的心思,怨谤君父。李定、舒亶一班小人,便把这个指作苏轼怨谤君父的证据,硬加他大不敬的罪名,要把他处死。神宗一时也被谗言所蔽,以为苏轼真个是逆臣。可巧被曹太皇太后知道了,召神宗进去问道:“听得现在诏逮苏轼下付台狱,苏轼究竟是犯了什么罪案啦?”
神宗对答道:“苏轼怨望朝廷,毁谤君父,犯着大不敬的罪名。”曹太皇太后惊道:“果然吗?苏轼何至于是呢?有证据么?”神宗对道:“有的。”即把苏轼作的诗歌,像前面摘出的,举诵数首作证。曹太皇太后听了,侧然道:“这个可作证据么?就这种无理的证据,就可认定苏轼是大不敬,要将他处死么?
须知文人制作诗歌,乃是一时的感触,并非有什么成见;就是有一二讽刺朝政处,这乃是诗人应有的态度。诗三百篇,不多是含着讽刺的吗?人君不能因而嘉念诗人忠君爱国的苦心,改善一切,反要罗织成罪,处以极刑,岂是人君慎狱怜才的道理?
当初苏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便重视他二人的才学,欣慰道:“朕为子孙得到两个好宰相了!‘而今诸人之指控苏轼,不是忌才,便是挟仇,不可不加熟察!”
神宗恍然,唯唯受教而退。吴充及同修起居注王安礼,亦上奏替苏轼解辩,神宗遂决意宽贷苏轼。王珪听得神宗要赦苏轼,忙再举苏轼的《咏桧》诗二句入奏。诗句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奏道:“苏轼这两句诗,显然是不臣的表证,若不严行谴责,将来把什么儆示后人呢?”神宗道:“卿何吹毛求疵一至于此!苏轼这诗,他自咏桧,何干朕躬呢?”王珪又奏道:“苏轼确系不臣,陛下必当重处才是。”神宗怫然道:“卿想使后世讥议朕不能容才么?”王珪才吓得不敢再奏了。舒亶又奏附马都尉王诜辈,与苏轼交通声气,朋比为奸;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亦与苏轼隐相联络,同一举动,都非严办不可。神宗不听,但从轻发付,谪苏轼为黄州团练使,本州安置;苏辙、王诜连坐削职;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罚锾而已。
一场文字狱,总算因曹太皇太后几句话,未曾小题大做,便轻轻地解决了。
苏轼奉旨出狱,即赴黄州治所。到了黄州,苏轼还是豪放如昔,常手策行杖,足登芒鞋,与田父野老,徜徉山水,载酒携琴,引朋挟妓,优游取乐。就东坡建筑一小室,满贮图书,作为居住的地方,自号做东坡居士。这所房子,虽系竹篱茅舍,却是精雅绝伦,净几明窗,古香古色。他常到人家饮酒,半夜才归。他的家僮都睡着了,他敲了半日门还是敲不开,便站在门前听听江流的自然音调,停一会再敲。
怎见得?有《临江仙》为证。词曰:夜饮东城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此时,还喜欢听人讲鬼,遇到人家没得说了,便道:“你只瞎说一回就是。”这是何等有趣的事啊!他的职位虽然是在官,而行径却异常浪漫,好像无拘无束的一般;每遇宴集,谈笑终日,一无倦容;间若醉后挥毫,真行参半,闳幽粲落,峻厉绝世。原来他的书法,少时习兰亭,后来又学颜鲁公,所以越加超妙了。当时那些营妓,见他不甚惜墨,争着跑来索题索书,拿回去增光斋壁。因此,苏轼的文名,益加洋溢起来。
神宗后来也爱他多才,想起用他作史馆修撰,终被王珪等多方阻扰,未果实行,只将他移徙于常州。这是后话。
神宗在十一年时,改元作元丰,此时已是三年了。忽曹太皇太后违豫,神宗乃与曹太皇太后弟曹佾同进慈寿宫省问病状。坐了一刻,神宗先起告退,意思想使曹太皇太后姐弟略叙私衷。不料神宗刚离座起,还未退出,曹太皇太后遽命曹佾道:“今日许尔进宫,已是偏在姐弟情分上,格外加恩的。尔当知道,此地不是尔得独留的,快随官家一同出去。”曹佾听了,连忙随了神宗出来。原来曹太皇太后一向不许曹佾入宫,也不许他干与国政。今日乃是神宗见得曹太皇太后病势不比往常,固请懿旨,才允许他入宫一面,毕竟不许他久留,可见曹太皇太后遵守宗法,虽属骨肉至亲,丝毫不肯宽假咧!过了两日,曹太皇太后的病益剧,神宗侍疾寝门,衣不解带,通宵守候,毫无倦容。最后一日,曹太皇太后自知将长辞斯世了,乃命宫女扶起,亲启金匮,取出章奏一束,亲手固封,付与神宗道:“待我死了开看,但只许儿自己明白此中故事,断不可因此罪人!”神宗含泪接收了。曹太皇太后又提笔写“博爱亲民”四个大字,作飞白书,笔势飞动,有游龙行空的气概,写完,钤盖慈寿宫宝,赐与神宗道:“这四个字,就抵得千言万语的遗嘱了,儿善体我的意思吧!”神宗忙跪下接受了,泣对道:“儿臣敬遵懿旨!”曹太皇太后听了,心甚欣慰,即命神宗起来。
神宗遵命起来,侍立一旁。曹太皇太后乃复卧下。停了一会,忽问宫女道:“今日是什么日时了?”宫女奏答道:“今日是十月二十日。”曹太皇太后颔首道:“呵!”又自语道:“只此日来,只此日去,免烦他百官。”说毕遂崩。原来这日乃是太祖皇帝大忌日,曹太后死在此日,省得别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的麻烦。当下神宗号啕恸哭,宫廷内外,齐放悲声。神宗哭了一会,群臣劝止。神宗乃启开曹太皇太后所授与的密缄观看。神宗阅罢,把它收在怀中,复又放声大恸,经群臣百般劝慰,才渐渐止住。你道曹太皇太后这封密缄里所藏的章奏,是议论的什么事情,神宗看了要这等哀恸?原来不是别的章奏,乃仁宗皇帝立英宗皇帝作皇嗣时,群臣谏阻的章奏,所以神宗看了要这等恸哭。神宗果然遵着曹太皇太后遗命,不追咎这些臣子,只自己感戴曹太皇太后的慈德,尽礼尽孝服丧。于是尊谥曹太皇太后做慈圣光献;推恩曹氏,进曹佾中书令,官家属四十余人。
曹佾及家属等,亦能遵慈圣光献遗志,虽蒙恩宠,无敢不谨的。慈圣光献丧事办毕,不觉又是三年六月了。
神宗因得自太祖皇帝开国以来,所有官制,多因袭唐朝,不过稍有异同罢了。
太师、太傅、太保,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不常置。以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别在禁中设置中书,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两柄,号做二府。天下财赋,悉隶三司。所有纠弹等事,属御史台掌管。至若尚书令、侍中、中书令,三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九寺;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司天,六监等,往往由他官兼摄,不设专官。草诏归知制诰及翰林学士:知制诰掌外制,翰林学士掌内制,号做两制。修史属三馆,便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首相充昭文馆大学士,次相或充集贤院大学土,有时设置三相,即分领三馆。馆中各员都称学士,一经此职,遂成名流。又有殿阁等官,亦分大学土及学士的名称。这些概无定员,大半由他官兼领虚名而已。
乃诏中书详定官制,设详定官制局,命翰林学士张藻,枢密副承旨张诚一主办这事。九月,官制议订完毕,凡旧有虚衔,一律罢去,改为官阶。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分作二十四阶。
领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等名,改为开府仪同三司;领左右仆射,改为特进;自是以下,易名有差。至此,宋朝才有了一定的官制。神宗因谓执政道:“新官制将行了,朕的意思,以为新旧两派人物,宜并行引用才好。”指御史大夫道:“这个官职,非用司马光不可。”王珪、蔡确听了,相顾失色。怎么唤做新旧两派呢?新派就是指维新的一派。这一派,奉王安石为首领,王珪、蔡确对于政治的观念,统是以王安石的政治观念为依归,系属于新派。旧派就是指守旧的一派。这一派,以富弼、文彦博、司马光一班人为首要。还有道学一派,以胡瑗、周敦颐、孙复、程颢、程颐、邵雍、张载一班人为首要,政治观念与旧派同,都是主张守旧的。
世称胡瑗作安定先生,孙复作泰山先生,周敦颐作濂溪先生,邵雍作康节先生,张载作横渠先生:诸人已先后死了。因为新旧两派是极不相容的,如果司马光见用,势必连类同升多人,大减新派的势力,且将摇动新派的政治地位,所以王珪、蔡确听了神宗说要用司马光,不由得要陡吃一惊。这时吴充已退职,王珪居首相,遂与蔡确商定个计策,荐俞充知庆州,使他上“平西夏策”,引得神宗专心戎事,便不召司马光。神宗乃任王珪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更命冯京为枢密使,薛向、孙固、吕公著为枢密副使,诏民畜马,拟从事西征。不久冯京、薛向并罢去,即命孙固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韩缜同知枢密院事。
忽知庆州俞充上奏,称夏将李清,本属秦人,曾劝西夏主李秉常以河西的地方来归。李秉常的母亲梁氏知道这事,立即把李秉常幽囚着,把李清杀了。这桩事件,我朝应兴兵问罪,此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神宗得奏大喜,即诏熙河经制李宪等,召集陕西河东五路的兵马,准备伐西夏,而召鄜延副总管种谔入对。种谔奉召,不敢怠慢,驰驿入朝。神宗问种谔道:“朕将亲征西夏,不知西夏的虚实究属怎样,卿且据实奏与朕知。”种谔这个人,生平最喜夸大口,乃是个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人,神宗偏偏召他入对,真乃问道于盲了。当下种谔便奏答道:“西夏没有人才,李秉常只是个小孩子,陛下大兵一去,就马上躧平了西夏,擒捉李秉常回朝了!”这正是:喜功好大终何益,误国只凭一语差。要知神宗听了这几句大话,信也不信,下回分解。
吴充意想将新法变革一二,自顾才学谫陋,乃奏请神宗召还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又举荐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神宗乃召吕公著同知枢密院事,进程颢判武学。程颢自扶沟县入京,任职才数日,李定、何正臣便劾他学术迂阔,趋向僻易,神宗仍命他还任原官去了。吕公著上疏谏阻,竟不得请。司马光在洛听得吴充颇有更正弊政的心志,乃致书吴充,陈述救济时弊的方法。司马光书云:自新法之行,中外汹汹,民困于烦苛,迫于诛敛,愁怨流离,转死沟壑,日夜引领,冀朝廷觉悟,一变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当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谋。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开言路以悟人主之心。
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为痼疾矣。吴充得书,颇想照司马光的意见,请神宗罢除“青苗”、“免役”、“保甲、”
市易“诸新法,广开言路以征求多士意见。蔡确听得,暗吃一惊,若是罢免了这些新法,引进忠良,他便要像化子没了蛇弄,不能再有饱饭吃,忙向吴充道:”这些新法怎能变更得呢?皇上费了多少勤劳,才得到今日的成绩,我辈好意思请求他废掉吗?而今只有萧规曹随,遵守前制,才是继往开来的善策。若一更变,便惹万代骂名了!“吴充听了,惧怕起来,不敢采用司马光的建议,仍旧履行新法。因此,王安石虽然罢了相位,新法却是一点也没有变更什么。
忽一日,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劾奏知湖州苏轼,怨望朝廷,毁谤君父,交通戚里,诚属大不敬,请严格究治。神宗大怒,降诏逮苏轼入都,下付台狱。原来苏轼前因论新法不便,谪贬杭州后,再徙于徐州,不久又徙湖州。他一路游山玩水,放情诗酒,消磨他郁郁不得志的烦恼岁月,也尝借着吟咏讥讽朝政。摘句如次:咏青苗云: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咏水利云: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课吏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咏盐禁云: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像这一类的诗歌,不胜枚举,原不过诗人一时感触,发为吟咏,并不是真个存着什么大不敬的心思,怨谤君父。李定、舒亶一班小人,便把这个指作苏轼怨谤君父的证据,硬加他大不敬的罪名,要把他处死。神宗一时也被谗言所蔽,以为苏轼真个是逆臣。可巧被曹太皇太后知道了,召神宗进去问道:“听得现在诏逮苏轼下付台狱,苏轼究竟是犯了什么罪案啦?”
神宗对答道:“苏轼怨望朝廷,毁谤君父,犯着大不敬的罪名。”曹太皇太后惊道:“果然吗?苏轼何至于是呢?有证据么?”神宗对道:“有的。”即把苏轼作的诗歌,像前面摘出的,举诵数首作证。曹太皇太后听了,侧然道:“这个可作证据么?就这种无理的证据,就可认定苏轼是大不敬,要将他处死么?
须知文人制作诗歌,乃是一时的感触,并非有什么成见;就是有一二讽刺朝政处,这乃是诗人应有的态度。诗三百篇,不多是含着讽刺的吗?人君不能因而嘉念诗人忠君爱国的苦心,改善一切,反要罗织成罪,处以极刑,岂是人君慎狱怜才的道理?
当初苏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便重视他二人的才学,欣慰道:“朕为子孙得到两个好宰相了!‘而今诸人之指控苏轼,不是忌才,便是挟仇,不可不加熟察!”
神宗恍然,唯唯受教而退。吴充及同修起居注王安礼,亦上奏替苏轼解辩,神宗遂决意宽贷苏轼。王珪听得神宗要赦苏轼,忙再举苏轼的《咏桧》诗二句入奏。诗句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奏道:“苏轼这两句诗,显然是不臣的表证,若不严行谴责,将来把什么儆示后人呢?”神宗道:“卿何吹毛求疵一至于此!苏轼这诗,他自咏桧,何干朕躬呢?”王珪又奏道:“苏轼确系不臣,陛下必当重处才是。”神宗怫然道:“卿想使后世讥议朕不能容才么?”王珪才吓得不敢再奏了。舒亶又奏附马都尉王诜辈,与苏轼交通声气,朋比为奸;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亦与苏轼隐相联络,同一举动,都非严办不可。神宗不听,但从轻发付,谪苏轼为黄州团练使,本州安置;苏辙、王诜连坐削职;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罚锾而已。
一场文字狱,总算因曹太皇太后几句话,未曾小题大做,便轻轻地解决了。
苏轼奉旨出狱,即赴黄州治所。到了黄州,苏轼还是豪放如昔,常手策行杖,足登芒鞋,与田父野老,徜徉山水,载酒携琴,引朋挟妓,优游取乐。就东坡建筑一小室,满贮图书,作为居住的地方,自号做东坡居士。这所房子,虽系竹篱茅舍,却是精雅绝伦,净几明窗,古香古色。他常到人家饮酒,半夜才归。他的家僮都睡着了,他敲了半日门还是敲不开,便站在门前听听江流的自然音调,停一会再敲。
怎见得?有《临江仙》为证。词曰:夜饮东城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此时,还喜欢听人讲鬼,遇到人家没得说了,便道:“你只瞎说一回就是。”这是何等有趣的事啊!他的职位虽然是在官,而行径却异常浪漫,好像无拘无束的一般;每遇宴集,谈笑终日,一无倦容;间若醉后挥毫,真行参半,闳幽粲落,峻厉绝世。原来他的书法,少时习兰亭,后来又学颜鲁公,所以越加超妙了。当时那些营妓,见他不甚惜墨,争着跑来索题索书,拿回去增光斋壁。因此,苏轼的文名,益加洋溢起来。
神宗后来也爱他多才,想起用他作史馆修撰,终被王珪等多方阻扰,未果实行,只将他移徙于常州。这是后话。
神宗在十一年时,改元作元丰,此时已是三年了。忽曹太皇太后违豫,神宗乃与曹太皇太后弟曹佾同进慈寿宫省问病状。坐了一刻,神宗先起告退,意思想使曹太皇太后姐弟略叙私衷。不料神宗刚离座起,还未退出,曹太皇太后遽命曹佾道:“今日许尔进宫,已是偏在姐弟情分上,格外加恩的。尔当知道,此地不是尔得独留的,快随官家一同出去。”曹佾听了,连忙随了神宗出来。原来曹太皇太后一向不许曹佾入宫,也不许他干与国政。今日乃是神宗见得曹太皇太后病势不比往常,固请懿旨,才允许他入宫一面,毕竟不许他久留,可见曹太皇太后遵守宗法,虽属骨肉至亲,丝毫不肯宽假咧!过了两日,曹太皇太后的病益剧,神宗侍疾寝门,衣不解带,通宵守候,毫无倦容。最后一日,曹太皇太后自知将长辞斯世了,乃命宫女扶起,亲启金匮,取出章奏一束,亲手固封,付与神宗道:“待我死了开看,但只许儿自己明白此中故事,断不可因此罪人!”神宗含泪接收了。曹太皇太后又提笔写“博爱亲民”四个大字,作飞白书,笔势飞动,有游龙行空的气概,写完,钤盖慈寿宫宝,赐与神宗道:“这四个字,就抵得千言万语的遗嘱了,儿善体我的意思吧!”神宗忙跪下接受了,泣对道:“儿臣敬遵懿旨!”曹太皇太后听了,心甚欣慰,即命神宗起来。
神宗遵命起来,侍立一旁。曹太皇太后乃复卧下。停了一会,忽问宫女道:“今日是什么日时了?”宫女奏答道:“今日是十月二十日。”曹太皇太后颔首道:“呵!”又自语道:“只此日来,只此日去,免烦他百官。”说毕遂崩。原来这日乃是太祖皇帝大忌日,曹太后死在此日,省得别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的麻烦。当下神宗号啕恸哭,宫廷内外,齐放悲声。神宗哭了一会,群臣劝止。神宗乃启开曹太皇太后所授与的密缄观看。神宗阅罢,把它收在怀中,复又放声大恸,经群臣百般劝慰,才渐渐止住。你道曹太皇太后这封密缄里所藏的章奏,是议论的什么事情,神宗看了要这等哀恸?原来不是别的章奏,乃仁宗皇帝立英宗皇帝作皇嗣时,群臣谏阻的章奏,所以神宗看了要这等恸哭。神宗果然遵着曹太皇太后遗命,不追咎这些臣子,只自己感戴曹太皇太后的慈德,尽礼尽孝服丧。于是尊谥曹太皇太后做慈圣光献;推恩曹氏,进曹佾中书令,官家属四十余人。
曹佾及家属等,亦能遵慈圣光献遗志,虽蒙恩宠,无敢不谨的。慈圣光献丧事办毕,不觉又是三年六月了。
神宗因得自太祖皇帝开国以来,所有官制,多因袭唐朝,不过稍有异同罢了。
太师、太傅、太保,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不常置。以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别在禁中设置中书,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两柄,号做二府。天下财赋,悉隶三司。所有纠弹等事,属御史台掌管。至若尚书令、侍中、中书令,三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九寺;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司天,六监等,往往由他官兼摄,不设专官。草诏归知制诰及翰林学士:知制诰掌外制,翰林学士掌内制,号做两制。修史属三馆,便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首相充昭文馆大学士,次相或充集贤院大学土,有时设置三相,即分领三馆。馆中各员都称学士,一经此职,遂成名流。又有殿阁等官,亦分大学土及学士的名称。这些概无定员,大半由他官兼领虚名而已。
乃诏中书详定官制,设详定官制局,命翰林学士张藻,枢密副承旨张诚一主办这事。九月,官制议订完毕,凡旧有虚衔,一律罢去,改为官阶。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分作二十四阶。
领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等名,改为开府仪同三司;领左右仆射,改为特进;自是以下,易名有差。至此,宋朝才有了一定的官制。神宗因谓执政道:“新官制将行了,朕的意思,以为新旧两派人物,宜并行引用才好。”指御史大夫道:“这个官职,非用司马光不可。”王珪、蔡确听了,相顾失色。怎么唤做新旧两派呢?新派就是指维新的一派。这一派,奉王安石为首领,王珪、蔡确对于政治的观念,统是以王安石的政治观念为依归,系属于新派。旧派就是指守旧的一派。这一派,以富弼、文彦博、司马光一班人为首要。还有道学一派,以胡瑗、周敦颐、孙复、程颢、程颐、邵雍、张载一班人为首要,政治观念与旧派同,都是主张守旧的。
世称胡瑗作安定先生,孙复作泰山先生,周敦颐作濂溪先生,邵雍作康节先生,张载作横渠先生:诸人已先后死了。因为新旧两派是极不相容的,如果司马光见用,势必连类同升多人,大减新派的势力,且将摇动新派的政治地位,所以王珪、蔡确听了神宗说要用司马光,不由得要陡吃一惊。这时吴充已退职,王珪居首相,遂与蔡确商定个计策,荐俞充知庆州,使他上“平西夏策”,引得神宗专心戎事,便不召司马光。神宗乃任王珪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更命冯京为枢密使,薛向、孙固、吕公著为枢密副使,诏民畜马,拟从事西征。不久冯京、薛向并罢去,即命孙固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韩缜同知枢密院事。
忽知庆州俞充上奏,称夏将李清,本属秦人,曾劝西夏主李秉常以河西的地方来归。李秉常的母亲梁氏知道这事,立即把李秉常幽囚着,把李清杀了。这桩事件,我朝应兴兵问罪,此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神宗得奏大喜,即诏熙河经制李宪等,召集陕西河东五路的兵马,准备伐西夏,而召鄜延副总管种谔入对。种谔奉召,不敢怠慢,驰驿入朝。神宗问种谔道:“朕将亲征西夏,不知西夏的虚实究属怎样,卿且据实奏与朕知。”种谔这个人,生平最喜夸大口,乃是个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人,神宗偏偏召他入对,真乃问道于盲了。当下种谔便奏答道:“西夏没有人才,李秉常只是个小孩子,陛下大兵一去,就马上躧平了西夏,擒捉李秉常回朝了!”这正是:喜功好大终何益,误国只凭一语差。要知神宗听了这几句大话,信也不信,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