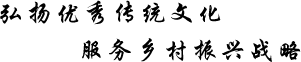苏门第一“愤青”苏辙

“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1963年4月,朱德委员长游览眉山三苏祠后,即兴题诗,称赞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道德文章,千古风流,堪与峨嵋比高。三苏父子皆名列“唐宋八大家”,苏轼、苏辙又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特别是苏轼,诗词歌赋,书画文章,无一不精,更是家喻户晓的大才子。苏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官场沉浮,经历坎坷,“乌台诗案”也让他成为古代文人因文字狱获罪的代表人物。历代文人,特别是年轻气盛的青年学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满腹经纶学问,汹涌澎湃,欲吐之而后快,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英勇气概现代人谓之“愤青”,这也正是年轻苏东坡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典型形象。然而,说到三苏父子中谁才是真正的“愤青”?那个人还真不是苏轼,这真正的“愤青”非苏东坡弟弟苏辙莫属。
苏轼、苏辙兄弟小时候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性格却差异明显。苏轼明快爽朗,苏辙沉默执着,据此他们的父亲苏洵在庆历七年(1047)为他们取了大名,并特意写了一篇寄寓深重的《名二子说》:“轼”为马车上用作扶手的横木,其貌不扬,却必不可少。“辙”为马车辗过留下的车轮印。苏轼啊,我担心你因不善于装饰自己的外表,而让你受到伤害啊。车会摔坏、马会死,唯有车辙安然无恙。苏辙啊,我知道你是可以免于灾祸的。苏洵解释了自己为两个儿子命名的缘由,对儿子满怀期望与祝愿。其时,苏轼十一岁,苏辙八岁。兄弟二人以后的人生轨迹似乎证明了苏洵的先见之明,而“轼”、“辙”这两字也似乎决定了兄弟二人的终身。
车辆纵横天下没有不留下辙印的,但对车辆创建的功劳,车轮印从来也不会参与争夺。车会被摔坏、马终究要死,唯有车辙安然无恙。这车轮印,是善于处在祸福之间的。苏辙的人生真的如父亲苏洵所言可以安然无恙,可以明哲保身、免于灾祸吗?实际上,在三苏父子中最先因文字获祸,最先因议论朝政遭遇打击的人,偏偏就是在父亲眼中沉着稳重、可以避免灾祸的“车轮印”苏辙。
苏轼、苏辙兄弟小时候被父母送到眉山天庆观北极院道士张易简处,接受启蒙教育。《东坡志林·道士张易简》载:“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苏辙也在《龙川略志》中说:“予幼居乡闾,从子瞻读书天庆观”。苏轼八岁时,苏辙还是幼儿,自然是哥哥的小跟班。苏轼兄弟二人从小在一起读书,未曾一日相离。苏辙在《祭亡兄端明文》中说:“手脚之爱,平生一人。幼而无师,受业先君。兄敏我愚,赖以有闻。寒暑相从,逮壮而分。”小时候的苏轼活波聪明,苏辙稍显沉默迟钝,年龄越大,区别越明显。其实,苏辙的聪慧是被哥哥闪耀的光芒掩盖了。
苏轼、苏辙兄弟长大后,又到眉山城西州学教授刘巨先生门下学习。刘巨先生学识渊博,要求严格,并且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充分发挥学生的特长。兄弟二人平时是以父亲、母亲为师,这一次系统地接受刘巨先生的正规教育,学问突飞猛进,特别在父亲不擅长的声律之学方面进步很快。兄弟二人开始吟诗作对,而且颇有天赋。苏轼有一篇《记里舍联句》,记叙当年兄弟二人在夏天大雨之时,与同学程建用、杨尧咨即兴联句赋诗。程云:“庭松偃盖如醉”,杨云:“夏雨新凉似秋”,苏轼云:“有客高吟拥鼻”,最后苏辙对曰:“无人共吃馒头”。座皆倾倒。苏辙最后这句对诗引发大家哄堂大笑,却体现了他的机智聪明,风趣幽默。你看,大家都在冥思苦想,一本正经地询章觅句,对景抒情,连吃饭都顾不上。程同学描绘雨中松树惟妙惟肖,杨同学让人感觉到下雨后的清凉,哥哥苏轼更是引用东晋政治家谢安“拥鼻”雅咏的典故:同学们,我们也来学学古人仿效谢安,掩鼻用雅音曼声吟咏。这时联句的气氛也一下子显得高雅起来。我苏辙可没你们那慢条斯理的兴致,肚儿饿了,对不起了,且让我先啃口馒头再说。苏辙边啃馒头边随口一对,那调皮的模样把大家都逗乐了。仔细想来,你别说,他的对句无论用词还是音韵都是蛮贴切的。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苏辙的对句画龙点睛,让整首诗活跃起来,情趣盎然,看似漫不经心,却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
苏洵早年喜好游历,二十七岁始发奋读书。庆历六年(1046),苏洵赴京赶考落榜后,对科举考试心灰意冷,他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苏轼、苏辙兄弟在父亲苏洵的严格要求下,寒窗苦学,博览群书,成为远近闻名的青年才俊。至和二年(1055),十七岁的苏辙娶同里史瞿之女、时年十五岁的史氏为妻。嘉佑元年(1056)春天,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兄弟前往都城东京(河南开封),参加科举考试。路过成都时,一同去拜访益州知州张方平。张方平之前就对苏洵的学识文章极为欣赏,相见恨晚,并向朝廷推荐苏洵。至和二年(1055) 苏洵带苏轼、苏辙兄弟拜见张方平后,张方平遂以国士之礼对待苏洵父子。据无名氏《瑞桂堂暇录》载,张方平还曾经当场出题考察苏轼兄弟。苏轼兄弟沉着应对,张方平十分满意兄弟两人的表现,他对苏洵说:“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 苏辙在宋哲宗元佑七年(1092) 出任门下侍郎,位至宰相,官位高于苏轼,此为后话。张方平随即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写信推荐苏轼、苏辙兄弟,并为他们准备了鞍马行装,派人送他们父子入京。
嘉佑二年(1057),苏轼、苏辙兄弟终于不负众望,高中进士。苏轼、苏辙兄弟具名列高等,苏轼登进士第二名,苏辙登进士第五名。当时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真可谓春风得意,少年得志。会试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副考官是著名诗人梅圣俞,两人正在锐意发起一场诗文革新运动。苏轼、苏辙兄弟清新洒脱的文风,深得他们的赞赏,故将他们同列进士高等。这件事引发出一场风波,欧阳发在《先公事迹》追述:“时学者为文以新奇相尚,文体大坏。公深革其弊,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几尽。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那些落榜的学子甚至上街围堵欧阳修,指责他录用这两个无名小卒。没想到,苏轼、苏辙兄弟反而因此名动京师,引得人人注目。欧阳修还特别赞赏苏洵的文章,把苏洵比作当代“荀子”,并将他的文章献诸朝廷。从此以后,“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曾巩《苏明允哀辞并序》)
北宋初年,朝廷上下都在倡导实用简洁、通晓流畅的文风,力戒五代时期的浮华奢靡,然而另一种追险务奇、故弄玄虚的文体又在悄然兴起,特别在国家最高学府太学中流行,时人称为“太学体”。这种文章风气来势汹汹,迅速弥漫朝野。就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即将夭折之际,一代文宗欧阳修力挽狂澜,开启崭新的文风,也让三苏父子作为这场文化变革运动的主将,脱颖而出。欧阳修是三苏父子的伯乐,没有他的欣赏、提拔,三苏父子恐怕会湮没终身。苏轼、苏辙兄弟从此以欧阳修为师,对欧阳修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苏辙在《欧阳太师挽词三首》中感叹:“推毂诚多士,登龙盛一时。西门行有恸,东阁见无期。念昔先君子,尝蒙国士知。旧恩终未报,感叹不胜悲。” 苏辙把欧阳修比作汉代德高望重的李膺,三苏父子被他接纳、推介如同“登龙门”,身价大增。苏辙对欧阳修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苏辙中第后,给当时的枢密使韩琦写了一封信《上枢密韩太尉书》。这是一篇干谒文,文章表达了对韩琦的仰慕之情及拜见之意,同时,苏辙简单介绍了自己求学为文的经历,明确提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对自己的文学主张进行阐述,这就是著名的苏辙“文气说”。苏辙写信虽为干谒,但行文中并没有流露出攀高枝、求高官的意思,态度不卑不亢,文辞恳切,引经据典,才华横溢。十九岁的苏辙给贵为宰辅之尊的韩大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韩琦也被这位青年人的卓越文采折服,大为欣赏。“自古英雄出少年”,苏辙就是最好的典范。毕竟苏辙当时只有十九岁,但他的“文气说”主张却新颖独特,别开生面,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撑,其远见卓识,令人惊叹!
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苏轼、苏辙兄弟能够崭露头角,横空出世,正是顺应了时代的需求。他们成功考中进士,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的老师刘巨先生,所谓“名师出高徒”,与他们同榜进士及第的还有他们的同学,眉山家安国、家定国兄弟,刘巨先生门下同时培育出了两对兄弟进士,一时传为美谈。苏轼、苏辙兄弟最直接、最长久的老师是他们的父亲苏洵,他们的文章风格深受苏洵的影响。苏老泉进士落第后,回家愤而尽焚旧作。闭门苦读,始得精六经,通百家,尤深于《孟子》、《战国策》,“下笔顷刻千言”。苏洵从小就有意识地培养苏轼、苏辙兄弟俩对春秋秦汉时期文章的喜好,反复训练指导他们的文章写作能力,并把自己的写作经验悉心传授。苏洵文章出入于纵横家,雄奇豪迈,被欧阳修视为“荀子之文”;苏轼烂熟《汉书》,初好贾谊、陆贽,既而读《庄子》,得心应手,为文浩荡无际,机趣横生;苏辙则深受《孟子》、《史记》影响,恬淡潇洒,气势如虹。三苏父子以文章名于当世,是他们成功的基石。然而他们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同样不能忽视,那就是官场人脉。苏老泉进士落第后,痛定思痛,意识到官场人脉的重要。所谓“哪管你才高八斗,就怕朱衣不点头”。科举考试不被考官看中,就是才高八斗也属枉然。李白早就感叹:“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在芸芸众生中能够被人欣赏、提拔实在是太难得了。苏老泉四处游历,结识不少朋友。他幸运地遇上了自己的伯乐雅州(四川雅安)知州雷简夫,雷简夫推荐三苏父子给益州知府张方平,张方平又推荐三苏父子给翰林学士欧阳修,而欧阳修正是这届科举的主考官。也可以说苏轼、苏辙兄弟俩的成功之路是父亲苏老泉铺就的,苏老泉的人生经验来自切身之痛。这也难怪苏辙小小年纪就敢斗胆给当朝枢密使大人韩琦写信干谒了。
就在苏轼、苏辙兄弟高中进士,等待吏部的选用,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嘉祐二年(1057)四月,母亲程氏去世,苏洵父子不得不回到蜀地奔丧。这一去就是三年时间,他们回到京城汴梁已是嘉祐五年(1060)二月。经吏部“铨选”,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河南宜阳)主簿,苏辙授渑池县(河南渑池)主薄。未及赴任,仁宗皇帝下诏制举,苏轼、苏辙兄弟于是留京应考。“制举”是皇帝为选拔人才举行的特殊考试,是一种最高规格的考试,要求极为严格。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员不但需要学识渊博,而且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然后由六名考官先行考核,及格者才能参加最后由皇帝亲自出题的考核。嘉祐六年(1061)八月,经欧阳修、杨畋推荐,苏轼和苏辙参加了制举考试。据记载,当时参加制科考试的只有四人,为什么人数这么少?据苏轼的学生李廌《师友谈记》载:“是时同召试者甚多。相国韩魏公(韩琦)语客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此语既传,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由此可见,苏轼、苏辙兄弟影响力之巨大。而相国韩琦对青年苏辙尤为关心器重。据说开科之前,苏辙偏偏生了病。韩琦于是上奏皇帝:“今年招考的学子,惟有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声望最高,而今苏辙病倒了,不能按时参加考试,必有孚众望,是否延期举行?”皇上竟然答应了。一直等到苏辙痊愈之后,才开科,考试推迟了二十天。后来以此为例,秋闱遂定在了九月。
试前,苏轼、苏辙按照规定,分别上了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各自阐述了治国理政的纲领。八月二十五日,仁宗在御政殿试,所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策问。“贤良方正”是说文学出众,道德端正,“能言极谏”是指善于策论,勇于给皇帝提意见。苏辙作《御试制科策》,这一次,他似乎是吃了豹子胆,文章矛头竟然直指年老尊贵的仁宗皇帝。也许真的是少年得志,趾高气扬,天不怕地不怕,苏辙身上的“愤青”气质彻底显露无遗。老苏毕竟没有经历过制举考试,他对儿子的考试也只能加以鼓励,却不料苏辙把父亲苏洵平时好为惊人之语的文章技巧充分发挥,从而闯下大祸,其激烈尖锐,令人咂舌!
苏辙在策论中指责仁宗怠于政事,甚至说仁宗“惑于虚名而未知为政之纲”。他说,仁宗在庆历新政时,劝农桑,兴学校,天下以为三代之风可以渐复,结果半途而废,未见实效。现在又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宽恤,或以省减,或以均税。苏辙认为这一切都不足以致治,因为各地所设官吏本来就是办这些事的,何劳再分遣使者巡行天下。苏辙一针见血地指出:“臣观陛下之意,不过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故臣以为此陛下惑于虚名也。”治国当择吏,皇帝当择宰相,宰相当择职司,“今乃不择贤否而任之,至于有事则更命使者,故臣以为陛下未知为政之纲也。”像这样指斥仁宗,顺带把为政的官员批评一通,真可谓咄咄逼人,不计后果。苏辙此时毫无从政经历,他的这些批评完全是书生之见。更为犀利的是,苏辙直接批评仁宗的私生活,指责仁宗沉溺声色。他一连列举历史上六个致乱之君(夏太康、商祖甲、周穆王、汉成帝、唐穆宗、唐恭宗),要求仁宗引以为戒,并说:“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治安,朝夕不戒,沉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罢,早寝晏起,大臣不得尽言,小臣不得极谏。左右前后惟妇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妇言是听。”他认为,仁宗所为与这些致乱之君相似:“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这样大胆的言论实在让仁宗颜面扫地。仁宗当时已经五十多岁,并非什么荒淫无道的君主,苏辙道听途说,未免夸大其词。苏辙还指责仁宗朝“赋敛繁重,百姓日以贫困,衣不盖体“,“官吏之俸”、“士卒之廪”、“夷狄之赂”以及“宫中赐予玩好无极之费”都要由百姓承担,因此“凡今百姓为一物以上莫不有税,茶盐酒铁,关市之征,古之所无者莫不并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宫中无益之用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无有。司会(主管财政之官)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
苏辙的批评虽然有些过火,但他直指当时国家冗官、冗兵、赋税沉重、对外屈膝等时弊,其胸怀大志、忧国忧民、忠君报国的赤子之心,坦坦荡荡,正气凛然。苏辙无所顾忌的批评立马在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大臣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主考官司马光在苏辙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他也曾经十九岁考中进士,他认为苏辙在应试者中表现出的爱君报国之心,可喜可嘉,拟如其兄苏轼评为三等;考官胡宿认为,苏辙试卷答非所问,又引历代昏君来比拟盛世英主仁宗,应该不予录取。更多的大臣认为苏辙狂妄自大,一致主张罢黜。幸运的是,仁宗皇帝不愧为仁厚之君,豁达大度,一锤定音:“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遗老斋记》)他欣赏苏辙的文章胆识,对苏轼、苏辙兄弟赞赏有加,还兴奋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于是苏辙入第四等次。苏轼在制科考试中相对中规中矩,文辞婉转,表现卓越,入三等次。宋朝开国一百多年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两人(《宋史·苏轼传》)。这是破天荒的大事,苏轼美名更是如日中天。当年苏轼二十六岁,苏辙二十三岁。考试结果,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作为京官被派往基层锻炼培养。苏辙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陕西商县)军事推官。然而,知制诰王安石认为苏辙袒护宰相,专攻人主,不肯撰写任命书。于是改命知制诰沈遘起草制词。多年之后,有人分析,说王安石是因为苏洵曾经写作《辨奸论》讽刺他,言辞激烈,从而导致王安石迁怒苏辙。这一说法并不成立。因为王安石曾为苏轼撰制词,而且颇为赞许欣赏。总之,“愤青”苏辙才入仕途,就栽了个跟斗。直到嘉祐七年(1062)秋,苏辙才得到朝廷任命。
事实证明,“愤青”终究会为自己过激的言行付出惨痛代价。《御试制科策》对苏辙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当时饱受舆论煎熬,担惊受怕,事后还被迫辞官,而且导致这位青年才俊多年一直仕途不顺。他晚年深有感慨地说:“予采道路之言,论宫掖之秘,自谓必以此获罪,而有司果以为不逊……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苏辙《遗老斋记》)苏辙对自己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深感失望。一气之下,他以父亲在京修《礼书》,兄长出仕凤翔,傍无侍子为由,奏乞留京养亲,辞不赴任。在凤翔任职的苏轼得知弟弟辞官决定,写诗《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劝慰苏辙,不同意他辞官的轻率决定。苏辙和诗《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为自己辩解,他在诗中说:“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虽然自己已经“学龟头缩”,“兼雉尾藏”,但是留京侍父只是借口,他的内心仍然孤傲,坚持己见,不肯低头。辞官无非是“避谤”,懒得听那些冷嘲热讽、蜚短流长罢了。“愤青”终究是“愤青”。
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结束在凤翔的任职,还朝判登闻鼓院,又试秘阁再入三等,得直史馆。于是,苏辙留京养亲的理由不再成立,他向朝廷乞官外任。苏辙被朝廷任命为大名府(河北大名)推官,不久出任管勾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哥哥苏轼可谓平步青云,弟弟苏辙却在边远之地,担任小小的幕僚,从事繁琐的文字伏案工作。治平三年(1066)四月,苏洵在京师逝世,苏轼、苏辙兄弟护送父亲灵柩,自汴河入淮,顺长江回到家乡眉山。次年十月,葬父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
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苏轼、苏辙兄弟服丧期结束后,返回京师。此时,朝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神宗皇帝励精图治,起用王安石,推行新法,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变法之初,诸法未备,神宗诏求直言。苏辙见年轻的神宗大有作为,不禁欢欣鼓舞,他奋笔疾书,一道《上皇帝书》,洋洋洒洒近万言。他在上书中说:“夫财之不足,是为国之先务也。”,欲治国必先理财,苏辙抓住根本,深入分析当前国家形势,“夫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而已。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查找导致国家危机的原因,“故臣谨为陛下言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要解决危机,就必须任用贤能,大胆改革。“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磨之以岁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苏辙慷慨陈词,虽然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但毕竟属于越次言事,内心诚惶诚恐,不知这道奏折上去,会不会又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哪知神宗看完苏辙上书,大为欣赏。即日破格在延和殿召见苏辙,听取他关于改革丰财的意见,并任命苏辙为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
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变法”组建成立的一个临时性机构,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三司条例司任用吕惠卿、曾布、苏辙等官阶低微的年轻人,参与草拟新法。每有新法出台颁布,王安石都组织他们商谈,征求他们的意见。苏辙在《龙川略志·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利害》对“青苗法”的产生过程作了详细记述。王安石拿出《青苗法》草案让苏辙仔细研究,苏辙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法看似惠民,实则伤民,倒不如采用汉以来各代推行的常平法,让富户商贾不能哄抬粮价,贫户也能得到切实的利益。王安石说:你的话有道理,我当从长计议再实行。他知道苏辙的“愤青”脾气,特别告诫苏辙“此后有异论,幸相告,勿相外也。”过了一个月时间,王安石都不再谈论青苗法。但后来王安石见青苗法在个别地方试行卓有成效,他就决定立刻颁布实施青苗法。此时的苏辙因王安石没有采纳自己的建议,“愤青”热血再次暴涨,他直接上书神宗《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表示反对。王安石大为恼怒,将加罪于苏辙,因副相陈升之的反对才作罢。苏辙一不作二不休,上书《条例司乞外任奏状》,请求离开条例司外任,“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真是典型的“愤青”做派。苏辙时年三十岁,仍然年轻气盛。所谓“前车之鉴后车之覆”, 苏辙并没从自己最初因直言而遭受挫折的惨痛经历中吸取教训,这一次又重蹈覆辙。其实,他身处变法大本营,只要稍加留意,依附顺从王安石,仕途青云直上是没有问题的。他的同事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后来都步步高升,贵为宰相。当然,苏辙二十多年后也担任了宰相,不过这升迁的道路也未免太曲折了。
神宗皇帝看完苏辙言辞激烈的奏章,感觉疑惑不解,问王安石:“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安石曰:“轼兄弟大抵以飞钳捭阖为事。”帝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续资治通鉴》)显然,神宗是支持王安石的。而王安石说苏轼兄弟“飞钳捭阖”即好出风头,邀功进赏的意思。这就完全曲解苏辙的赤胆忠心了。苏辙看见一项危及老百姓利益的政策即将出台时,就奋不顾身,为民请命,其精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幸好神宗并未同意王安石加罪苏辙的建议,准予苏辙离开三司条例司。秋末,苏辙在三司条例司呆了短短五个月时间就被迫离开,出任河南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春,张方平知陈州(河南淮阳),聘任苏辙为州学教授。这是苏辙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一个锐意进取,勇于改革的优秀青年,转眼间被时代抛弃,划入到反对变法阵营,甚至成为旧党的中坚力量。这到底是苏辙个人的无奈选择,还是是“王安石变法”,乃至整个大宋王朝的悲哀呢?
苏辙从当时的最高权利中心一下子被下放,出任地位低微的州学教授,其内心的愁苦愤懑是可想而知的。苏轼对弟弟受到的挫折深表同情,经常写诗去信问候。紧接着,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也因反对新法出判杭州,他在《戏子由》诗中写到:“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虽为安慰弟弟,但苏轼仍然改不了他好开玩笑的习惯。“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别驾(杭州通判)旧齐名。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他们两人都才三十来岁,哪里谈得上衰老,但苏轼对弟弟说公道自在人间,不要灰心丧气。“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面对打击,我们更要坚持读书人的风骨。这首《戏子由》后来也成为苏轼讽刺新法的证据之一。苏辙的好友、亲家翁文同对苏辙也很关心,二人常有书信往来。文同到陵州任太守时,作《子瞻〈戏子由〉依韵奉和》寄给苏辙,诗中写到:“子由在陈穷于丘,正若浅港横巨舟。每朝升堂讲书罢,紧合两眼深埋头。”,“贫且贱焉真可耻,欲挞群邪无尺箠。”对那些欺负苏辙的小人,他恨不得拿起尺箠(鞭子)加以痛打!“安得来亲绛帐旁,日与诸生共唯唯。”虽然苏辙的年龄比文同小得多(二十岁),但文同表示愿意当他的学生。“君子道远不计程,死而后已方成名。千钧一羽不须校,女子小人知重轻。”文同认为苏辙为道义而献身的精神非常可贵,这一点就是妇女儿童都是明白的。文同的鼓励无疑是对苏辙的最佳抚慰。
在神宗朝,苏轼虽不得志,但他三典名郡(密州、徐州、湖州),是风风光光的地方长官;而与苏轼才华相当的苏辙却一直作幕僚,从事教学、文案工作,直至四十七岁才作了“县城如手大”的绩溪(安徽绩溪)县令,够倒霉的了。苏轼身上也有“愤青”气质,但相对苏辙,他人情练达,应对官场往来,经验要丰富得多。苏轼的诗文风靡全国,广为传颂,出尽风头,他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并未发表多少反对讽刺新法的过激言论,遭遇的文字灾祸多出于别人捕风捉影的嫉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苏轼自然成为被攻击的首选对象,而他的几次遭遇灾祸都牵连到苏辙,一起遭殃。反观苏辙,他连皇帝的错误都敢指责,对富弼、王安石等宰辅级别的官员更是毫不留情地直接批评,这才是典型的“愤青”风范。这两次“愤青”事件的不利影响,教训实在太惨痛。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苏辙因此而得以远离权力中心争斗,一直困于基层,避免了更大的灾难。这还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苏洵“车轮印”预言的先见之明。
北宋后期,党争激烈。苏辙的政治生涯也随着党争的起伏演变而沉浮。那曾经的“愤青”已经不再年轻,但无论是身处朝堂,贵为宰辅之尊,还是遭受迫害,贬谪到荒凉的瘴疠之地,苏辙肩挑道义,见义勇为,敢于直言的精神始终没有改变。苏辙在《亡兄端明墓志铭》中对苏东坡的性格特征描述道:“其予人见善者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者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斯不顾其害”。这段话无疑也是对他自己“愤青”性格的最佳注脚。
暮年的苏辙退居颍川(河南许昌),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他深居简出,不问世事,甚至多年闭门不通宾客。为了避祸,他曾经只身逃往汝南(河南汝南),不敢回家,在汝南居住一年时间。也许可以用辛弃疾的《丑奴儿》这首词来形容暮年苏辙的心境:“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十月三日,苏辙盍然离去,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四岁。
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东津路6号 刘永